身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享受包场电影的待遇了,记忆中最早的一次,是在史家胡同小学礼堂看《蝙蝠》,吓得钻到椅子下面。那时候看的不外乎都是些主旋律影片,其实看什么是次要的,主要是电影院里都是自己人,就算看的是恐怖片,也能保证受惊吓程度有限。
后来看露天电影,晚上的电影,吃过午饭便要拿小板凳去排队,往往我是最先到,一个人坐在空旷的场地中央,看着他们挂上白色的银幕。接下来便是绝望的看着身边黑色的大人们越来越多,直到他们把空旷的球场全部填满的过程,就这样,到了晚上电影开演的时候,我往往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只能垂首聆听电影的对白。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一个不受打扰,永远不用去提前占座的这么一个地方,就在银幕的正前方,刚好被银幕上投射出的一束光罩住。
后来有了电影院,记忆中,无论放什么电影,永远都是满座,第一排也不例外。再后来,有了循环播映的录像厅,再后来,录像厅里有了包厢。我的第一次表白,就是在一次通宵录像里。第二天凌晨走出那个录像厅的时候,历史就这样被改写了。
那天晚上的录像,是我们两个人的包场。但奇怪的是,我完全不记得那天晚上银幕上发生了什么,这也难怪,银幕下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
自从那天开始,电影院或是录像厅里的人,就越来越少,满座的情景越来越像是一个传说。两个人的包场,还发生过多次,我清楚记得我身边的那个人,也清楚记得银幕上的故事。有一次是和龚总,看的是《超人总动员》,有一次是和阿黄,看的是《世界》,还有一回是和娜娜子因为工作原因而看的《非诚勿扰》。奇怪的是,这些电影都是好电影,相反,当初看《无极》的时候,因为满座我却享受了一回加座的待遇,可见,银幕下的观众人数和电影质量,实在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就在今天,我们又享受了一回电影包场的待遇,电影是《万箭穿心》,观众是我,阿黄和老姚。对于上影永华来说,电影开场前3分钟卖出去的这三张票,实在不知道是喜还是愁,但对于我们来说,绝对是一个惊喜,在发现只有我们三个老男人后,阿黄把脚翘上了前排的椅背,老姚则放肆地抽起了烟,并宣称这是他第一次抽着烟看电影。而我,则沉浸在一连串亲切的“婊子养”里。
《万箭穿心》是部好电影,和去年的《最爱》一样,它奉献出今年中国银幕上最伟大的一次集体表演,无论是第一男配角建建,还是颜丙燕的婆婆,或是其他仅有只言片语的龙套,或许是因为说方言的缘故,表演松弛传神,和电影,和武汉这座国际大县城融为一体。相比之下,颜丙燕的表演倒是由于用力过猛,以及蹩脚的武汉话,成为一个让人不断出戏的短板。在影片里,她成为了她家庭的局外人,而对于我的感觉而言,她也游离在影片的边缘。影片让我很震惊,我震惊于演员表演的惊艳,还震惊于开场就铺天盖地而来的“婊子养的”。这四个字,基本就是武汉的名片,它就这样堂而皇之和汉正街的扁担,和底层人住的通铺一起出现在电影银幕上。巧的是,我昨天刚看了另一部国产片《房不剩防》,里面也出现了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住20个人的场景,不同的是,《房不剩防》是一部喜剧片,它利用这个超现实的场景制造出了一个段子,回避了它的本质,而《万箭穿心》则正视了这个现实,正视了武汉最破败最落后最肮脏的这一面。
很多细节是非常有意思的,颜丙燕在江边独坐,遇到过生日放烟花的年轻人,片尾车子熄火的镜头等等,很多。武汉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截取细节,就好像在香格里拉拍照一样,不用构图不用刻意摆拍,拿镜头随便一扫,从取景器里看到的都是只有两个字:牛逼。香格里拉的牛逼是它的美,武汉的牛逼是它的俗。记得上一部这样做的是《生活秀》,但可惜的是,那部影片是在重庆取景,你要说它有多大的缺点倒也未必,就像罗斯列举了瑞秋的缺点和其他女人所有的优点之后,叹一口气说,她只有一个缺点拿就是她不是瑞秋。《生活秀》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是武汉。
说到美,《万箭穿心》或许是刻意为之,它几乎没有一个镜头是称得上美的。40岁的颜丙燕不美,她的闺蜜,她老公的情人,都年过40,体态开始臃肿开始步入中年妇女行列,而男演员里也没有一个称得上帅哥。影片的取景,在汉正街上,在破旧的居民楼里,在颜丙燕被强奸的那辆打不着火的微面里。其实我觉得,武汉是中国最真实的城市,而《万箭穿心》无疑是到目前为止,对武汉这个城市的最真实的塑造。武汉曾经是中国最洋气的城市,它也是最粗俗的城市,它曾经是最激进的城市,也是最保守的城市。只有在武汉呆过,你才能真正领悟到这种属于中国的辩证存在。
说到扁担,我在95年呆在武汉的那几年里,所在的办事处长期雇了两个搬运工,一个姓张一个姓吴,他们年过60,不识字,领着一个月300的工资,每当有货运到,他们就承担起卸货的重任。离开武汉之后,我几乎从未回忆起他们,但在看完电影的这个夜晚,我突然就想起了他们,在颜丙燕的身上,我看到了他们的影子,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颜丙燕的一生。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干不动而退休的,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死去或将要死去。他们和我呆过的办事处早就撤销了,而我第一次表白的录像厅也早就不在了,只有这块银幕,还忠实地守护着我们的记忆。
这样一部由40岁以上的演员拍摄的、全片说武汉方言的、以武汉的阴暗面为主要拍摄场景的、几乎没有配乐的、摄影也从头难看到尾的电影,能在黄金时段出现在一块中国的银幕上,我很难过,但我更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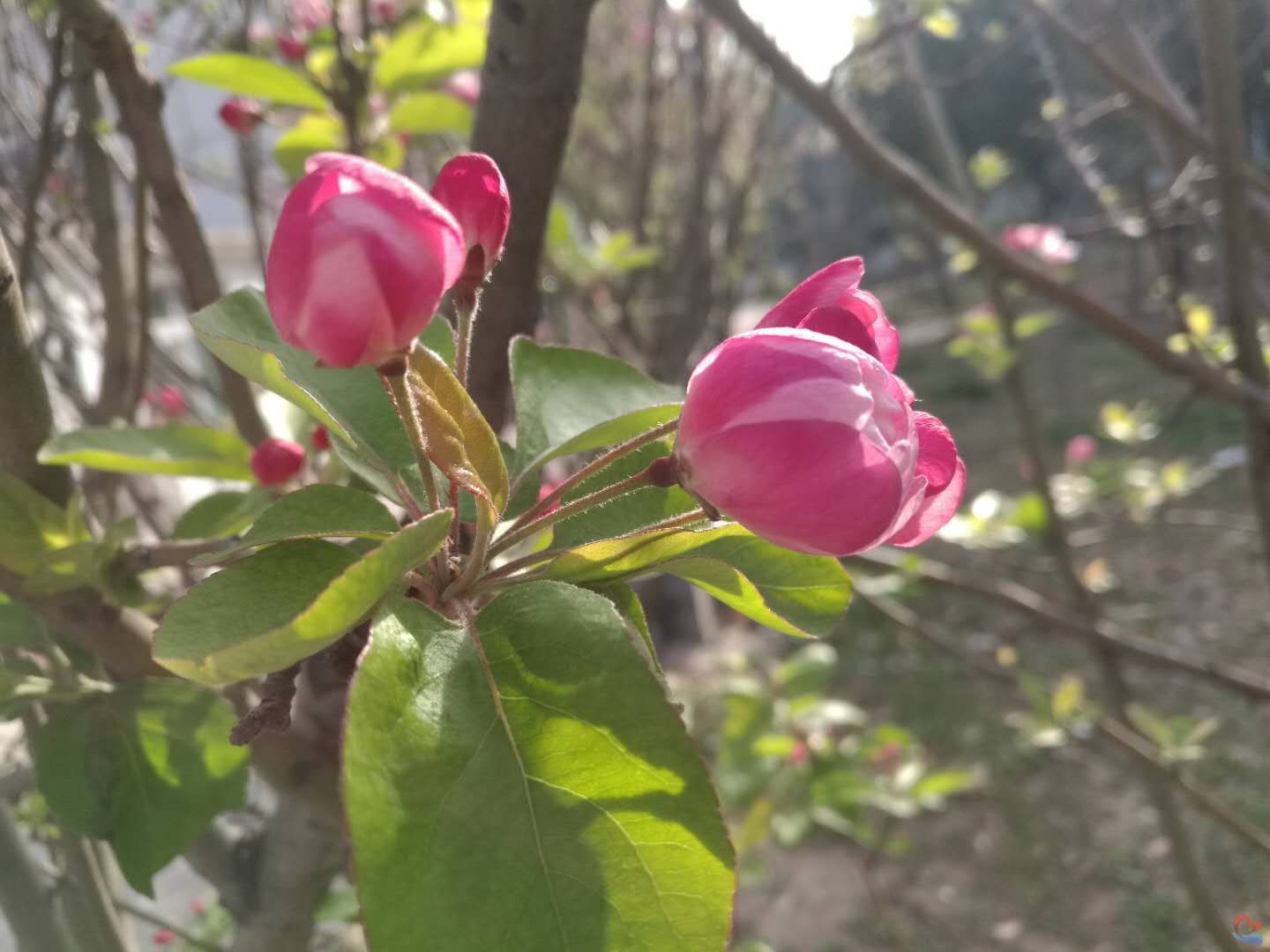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