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你是文学爱好者,那么到了上海,去武康路113号的巴金故居走走,不失为是一处感悟文学和搏动心灵的地方,这里是中国文坛大师巴金先生生前居住的地方。清明节前夕,我怀着敬仰的心情走进了巴金故居,这是一幢矗立在绿树花丛中的浅灰色的三层独幢花园洋房。
那是1955年5月,巴金和夫人萧珊就迁居到了这里,当年10月,他就在此迎接了第一批客人——法国作家萨特和同为知名作家的爱人波伏娃。另外,还有著名作家夏衍、沈从文、曹禺、柯灵、王西彦、唐弢等文坛名人都陆续来到这里,成为这里的座上客。巴金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这是巴金先生在上海定居最长的地方。
巴金在文学创作上一直主张作家要下去,创作要上去。在这处故居里,巴金写下了中篇小说《团圆》。这是巴金实践着自己的创作原则所诞生的优秀作品。当年,他作为志愿军慰问团的成员,在朝鲜战场住过很长时间,为了采访英雄人物,他冒着飞机炸弹和枪林弹雨的极大危险,终日在战壕里与志愿军指战员同甘共苦,作品中的“英雄儿女”就是他用生命写出来的。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成为那一个时期观众最多的家喻户晓的电影之一。除了《团圆》等小说外,他还写了《倾吐不尽的感情》、《赞歌集》等多本散文集,还翻译了《往事与随想》等文学名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也在晚年完成于此。
武康路113号地处市中心,是一处闹中取静的地方。庭院绿树成荫,花草茂盛。洋房是由一栋主楼、两栋辅楼和一个花园组成,总占地面积为1400平方米左右。楼是假三层,细卵石墙面,深绿色的木窗,白色的拱形门,每到盛夏季节,墙上和窗边爬满了青绿色爬山虎藤蔓,靠墙有一个木制楼梯,简洁而典雅。
故居墙上挂着一块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在1999年9月23日设立的“优秀历史建筑”铭牌,上面写着:“花园住宅,曾为苏联商务代表处。1923年建造。假三层,细卵石墙面,装饰简洁。南立面底层为敞廊,上为跌槽式山墙:北立面入口设带卷心石的半圆形拱券。”。
抬头望,楼房分为主楼、南北两侧配楼和一个花园,这里还有一间向阳的阳光间。门厅正前面挂着一幅巴老开怀欢笑的照片;墙上,挂着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的水墨画上的巴金图。红梅丛中的巴金,被画家在巴金刀刻般的肖像周围,独特设计了五线谱线条的树枝,红梅点点,相映在那张古典的面孔上。只见巴金银发竖起,看似凌乱,但富有坚韧不拔的力度。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是巴金的忘年交好友,这幅画是画家心中最真实的晚年巴金,它暗示了一代文学大师旺盛的文学生命力。画上,还配有黄永玉的诗《你是谁》:
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是战士,还是刚出狱的囚徒?是医生,还是病人?是神父,还是信徒?是作曲家,乐队指揮,还是嘹亮的歌者?是牧人,还是羊?是摆渡者,还是河?是远遊人,还是他背上的包袱?是今天的熊猫,还是十几万年前的恐龙化石?
你带领过无数学龄前儿童走向黎明。你是个被咬掉奶头、扪着胸痛的孩子他妈。 你永远在弯腰耕耘而不是弯腰乞食。你是沉默忍受煎熬的“拉孔”,从不叫出声音。谁都认识你是“巴金”,你大声喊出: “我是人!”
黄永玉先生写的诗中的“拉孔”,为“拉奥孔”的早期译法。〔拉奥孔,指的是大理石群雕,高约184厘米,是希腊时期的雕塑名作。阿格桑德罗斯等创作于约公元前一世纪,现收藏于罗马梵帝冈美术馆。〕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青年时在“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下,他渴望自由,是一个大胆、叛逆,富有理想和热情,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憎恨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万千投身革命洪流中的热血青年之一。 1923年,他离家赴南京和上海求学,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后来在法国留学时,他仍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以无畏的探索和反抗精神,伴随着巴黎圣母院孤寂的钟声,写下了中篇小说《灭亡》。回国以后,他又积极参加抗战活动,担任《救亡日报》编委,从此走进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之路,成为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
提起“巴金”的这个笔名,内含着一个难以忘怀的友情故事,他的笔名是为了纪念亡友而为。还是在1957年,他在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对自己的笔名作了注解,其中的故事是这样的:那是1928年8月,巴金写好小说《灭亡》时,准备在原稿上署个笔名,忽然他想要找两个笔画比较少的字。当时他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看到了文字中有一个“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了下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一个姓“巴”的朋友突然自杀了。这是一个当年和他在法国留学期间住在一起的朋友,虽然居住的时期不是很长,但两个人的感情颇深。听到朋友去世的消息,巴金太悲伤了!想到和朋友在巴黎一起生活过的那些难忘日子,巴金决定定用笔名记住“巴”朋友,就很快在“金”字的前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他一生中永恒的笔名,这个笔名通过他的众多书籍走进了千家万户。然人们没有知道,在巴金这个名字中竟包含着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同时也凝结着巴金对朋友的浓厚真情。
走进小洋楼,从门厅过去,右面一间是客厅,立于墙壁的大多数是书柜,书柜里除了摆放着巴金的各类著作,还有他生平收藏的各种书籍。这间客厅,也是巴金会见亲友和朋友的地方。除了弟弟李济生等外,还有各路文学家和书画界的朋友师陀、孔罗荪、王西彦、柯灵、张乐平等。这间客厅也是1982年意大利的“但丁国际奖”和1990年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向他颁奖的地方。客厅的壁炉上是林风眠赠送给巴老的“鸳鸯图”。
看到这客厅,我忽然想起八十年代中旬,我在北京拜访沈丛文先生的时候,沈老告诉我:他和巴金是文学上的知交,他于1974年曾专程到上海看望了病后的巴金,两人坐在一楼的走廊上促膝长谈,彼此对生活和创作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现在,他们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微笑,仍然凝固在这间客厅的镜头中,沉淀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中不忘。
看到巴金的书柜和他的书,就会想起读他作品的那些日子。记得我第一次读巴金的作品是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当时我是学校图书馆的学生管理员,每天中午时间负责和老师一起值日,接待前来借书的同学,在这期间,我利用空余时间,阅读了巴金的作品《家》。此书语文老师也辅导介绍过,因此对作者充满了好奇。
那是六十年代中旬,我经常坐在中学图书馆的桌子上贪婪地读,虽然那时的理解和鉴赏能力浅薄,但总是被书中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境遇深深吸引。小说《家》以“五四”运动浪潮波及的滞塞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高公馆这个“诗礼传家”“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分化过程,故事集中在1920年冬到1921年秋的时间里,揭露了封建专制的腐朽本质,控诉了封建家庭制度、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罪恶,赞颂了年轻一代的反抗斗争精神;通过对青年一代勇敢抗争的描写,展现了在严密残酷的黑暗王国里放射出的一线光明,充满了时代气息、希望和力量。作品撕开了在温情关系掩盖下的大家庭的勾心斗角,暴露了所谓“诗礼传家”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无耻,描写了新思潮听唤醒的一代青年的觉醒和反抗,从而宣告了这个封建大家庭必然崩溃的命运。通过读他的书,我记住了“巴金”这个文学巨匠的名字。并且在心中孕育了创作的欲望。
巴金故居的底层南面原来是敞廊。1982年,巴金在楼上写作时不慎摔倒,腿脚受伤。在巴金住院期间,家人为方便巴金写作,在一楼开放式的长廊上加了几扇窗户。阳光透射,窗挡住了风,冬天,这间房子被称为“阳光间”;夏天,开窗凉风习习。“阳光间”里摆放着书柜,还有一张是用缝纫机改成的书桌,轮椅上放置了一块用来写字的木板。晚年的巴金一直喜欢在这“阳光间”艰苦写作。这里是被称之为是冬暖夏凉的地方。
“太阳间”是巴金受伤后散步的地方。他常常坐在椅子上晒晒太阳,思考和构思写作。晚年的他患有帕金森氏症疾病,有时手抖得不行,他仍坚持写作,这种执着展示了他的一颗美好的文学心。巴金一直在这里坚持写作,一直写到95岁。是什么力量让他具有如此的坚持不懈的写作意志和毅力?我想,这就是他对文学执着的爱,如果没有这样的爱,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毅力和力量,就不可能成就他的文学事业!有人说,巴金的《随想录》就是这样用手抖出的。看他的画像,就像一樽雕塑,凝固的在参观者的眼前,靓得鲜活起来。
二楼有书房、客厅、卧室。书房里摆有几个大书柜,都装满了书。紧靠楼梯左边的书柜,装满了外文书籍。这些书籍都是他使用过的工具书。有大英辞典、牛津辞典、俄汉成语小词典、德语动词、汉法词典、现代瑞典语辞典、世界语分析语法、日本姓名词典、袖珍音乐小辞典、标准歌剧和音乐会手册等等。
理想和信仰点燃了巴金心中的激情,点燃巴金的勇气。巴金懂多国文字,他不仅是一个著名大作家,也是一个影响力的翻译家,他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名著,如《高尔基短篇小说集》,屠格涅夫《父与子》、《处女地》,赫尔岑《家庭的戏剧》、《往事与深思》,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的自传》等,译著达60多部;客厅中央放着一个大茶几,四周摆着长短沙发;卧室是夫人萧珊使用的。
三楼是一个阁楼,称为“假三层”,这是巴金的书库,藏书近8万册,可见他的阅读量大得惊人。难怪他能取得这么大的文学成就,巴金是学到老,写到老的典范!巴金爱书,在中国文学圈内是出了名的。早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了,但他省吃俭用,仍要坚持买书。一天,一向依着他的萧珊实在忍不住对他说:“你知道吗?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
但爱书如痴的巴金说:“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第二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他就是这样,一生淡泊金钱名利,为文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就是由他倡议并拿出自己的稿费出资创建起来的,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他就倡导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且带头捐出十五万元的稿费,还有他平生收藏的八千多册现代图书及很多珍贵的书画手稿,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中国现代文学保藏了丰富的资料。199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中心,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于一身的中国最高文学殿堂,2000年5月对外开放。
巴金和夫人萧珊的感情深厚,在文学界堪称典范,简直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传为美谈。1936年,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年轻一代对幸福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此时巴金收到了许多书信,很多是追求他的女性写来的。在众多的女性中,有一个高中女生给他写的信最多,那女孩是浙江宁波鄞县人,名字叫萧珊,生于1918年1月8日,比巴金小13岁。她是第一个也是惟一让巴金生活中最动情的女人。1936年萧珊到达上海,在爱国女子中学读书,她是文艺积极分子,喜欢参加学校戏剧演出,曾参演过戏剧家曹禺在1933年撰写的四幕话剧《雷雨》,她在剧中扮演了梦幻纯真的四凤。话剧中的四凤是花季少女,正处在做梦的年纪,神差鬼使让她遇到周萍,她怎不芳心暗许,周萍的忧郁吸引了四凤,让天性善良的四凤心生怜悯,她选择了幽暗的周萍而不是阳光少年周冲。在一片暴风骤雨间小心谨慎生存的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小心追求的幸福自由却是恐怖的无底深渊,她恋上的竟然是自己的亲哥哥,而且还有了身孕,于是她毅然含恨而去。世人怜悯她,惋惜他……这出话剧演得催人泪下。
她和巴金的通信长达半年之久,但却从未见过面。最后,还是萧珊在信中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 萧珊主动寄了一张照片给巴金。那天、巴金又拆开了一封信,突然,一张女孩子的照片从信中掉了出来。他很诧异地拾起照片看了看。这女孩剪着一头短发,额前还覆盖着刘海,她头上戴着花边草帽,身着白衣黑裙,一脸天真稚气的笑容。下意识地翻过背面看了看,上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然后他们相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
在这一过程中,萧珊在巴金鼓励下,开始了文学创作。1937年,她发表了第一篇写抗战随笔的题材散文《在伤兵医院中》。此文发表在著名作家茅盾主编的《烽火》杂志上。中学毕业之后她随巴金西行,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他们经过了长达8年的恋爱期,年届不惑的巴金被姑娘的执着所感动,直到1944年5月1日,40岁的巴金和27岁的萧珊结了婚。婚后,巴金对萧珊恩爱有加。新中国成立后,萧珊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任《上海文学》、《收获》编辑,兼任文学翻译。在巴金的鼓励下,萧珊的创作也非常勤奋,著作有《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萧珊文存》等,译作有屠格涅夫的《阿细亚》、《奇怪的故事》、《初恋》以及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等。1972年萧珊身患癌症,手术后五天病逝于上海。病逝后,巴金将萧珊的照片和翻译的作品一直放在床头,还把她的骨灰盒放在左手边的五斗橱上。他说这样每当看到她的书和骨灰盒,就会想起一起走过的难忘岁月,就像她永远在我身边一样。有人劝他把夫人的骨灰安葬,他不同意,坚持把夫人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卧室里,他说这样才能感到夫人仍然和他在一起。他在文章中这样说,“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萧珊的骨灰盒放在巴金的房间里,这一放就是整整三十三年的时间,可见他和萧珊间的爱情是多么的深!他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写道:“她是我的一个读者。1936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和她见面。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20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深藏着一位作家多么博大深厚的情怀!
在萧珊离开他第十二年时,巴金又深情地回忆:“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门口,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可是走进院子,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上了台阶,我环顾四周,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为什么偏偏她的面影不能在这里再现?”
1999年2月8日,巴金患了呼吸道感染突然高热,出现了急性呼吸衰竭症,被送往华东医院抢救,从那天开始他的病情反复波动。从此,整整6年巴金没有离开过医院,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张他不想住的病床。巴金曾多次向家人提出要安乐死,但被拒绝,他为此还发过火。2005年4月,巴金被发现腹部腹水。经过反复会诊、检查,诊断为腹腔间皮细胞瘤。10月3日,胃部出血。一周后的10月13日腹腔大量出血,确诊为恶性间皮细胞瘤。尽管医生想办法尽力地抢救,但最终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
2005年10月17日,101岁的巴金离世,这位跨越了两个世纪的老人,见证了世纪的沧桑巨变。他从热爱文学开始,始终紧握手中的笔,书写历史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以及时代前进的脚步。根据巴金生前的遗愿,他离世后要将自己和萧珊的骨灰一起撒向东海。他在《怀念萧珊》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巴金去世后,家人遵从他的愿望,将两位老人的骨灰撒入东海的万顷波涛。
那是2005年11月25是巴金101岁诞辰。清晨,巴金和夫人萧珊的骨灰在家属和友人送行下乘船来到吴淞口,在巴金生前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声娓娓响起时。他的骨灰和夫人萧珊的骨灰一起随着鲜红的玫瑰花瓣撒入东海……他们一起结伴魂归天国。巴金那颗永远燃烧的心和不老的魂灵,和夫人萧珊一起变成东海的浪花,开在中国文学的花海里。巴金去世后,2012底,武康路113号经修缮后作为巴金故居和纪念馆向社会开放。
在巴金故居的展柜中,还有巴金夫人萧珊当年使用的上海公交月票、手包、穿过的外套、“上海”牌手表等生前用过的东西,还有萧珊上世纪60年代的就诊记录卡,还有巴金《怀念萧珊》的手稿,淡蓝色的笔迹记录着两人经历的风雨,抒写对亡妻的深情,这种坚贞不屈的爱情在中国是少见的,这会使观众能够从中看到一个真实立体的萧珊。
巴金故居忆巴金。在巴金的故居行走,使我不由想起1989年夏在北京民族学院家族宿舍拜访文坛大师谢冰心时的情景。那天午后,我随全国优秀辅导员夏令营中的十余位文学爱好者一起,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缪力女士的带领下,乘上中巴去拜访冰心大师,聆听她的教诲,听她讲如何为少年儿童进行文学创作,谈《三寄小读者》的写作。冰心大师坐在不锈钢制作的代步车内,又说又笑。当我们来自基层第一线的教师介绍自己的工作和创作情况时,冰心大师很高兴地点头微笑点赞,一连说了好几个“好”!轮到我作自我介绍,话音还没落,冰心大师就说:“好呀,你是从上海来的。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我以前去过上海多次,那里有我的巴金老弟,他写的作品很多,也有为少儿写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她还说:“后来我们一个住在北京,一个住在上海。但时空隔不断我们的通讯交往,我们经常写信或者打电话,他以前和老舍先生一样吃的苦很多,他去过‘五七’干校,可怜的妻子很早就走了,他很不容易,守着妻子的骨灰忠诚不渝。我们之间也是文学知音,深情如海,在特殊年代里,我们依然关心着文学。我的脚走路不方便,否则我会去多看看他……”她老人家还说:“巴金是最可爱最可佩的作家,他追求‘说真话’,‘大憎和大爱’、‘爱得深切’、‘憎得鲜明’,也是我最疼爱的老弟之一。你如回到上海时见到他就代我问候他好……”可见两位老人的友谊是多么真诚。
回到上海后,我去看望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的我的文学老师谢泉铭,在谈到北京之行拜访冰心大师的事,我把冰心大师带信的事告诉了谢泉铭老师。谢泉铭老师当场拨打了巴金家的电话,但没有人接。我就请谢泉铭老师转达冰心对巴老的问候。后来,每每想起冰心大师那弥坚的声音,总觉回响耳边……
巴金故居忆巴金。我不由又想到了2017年1月18日,当我带着380万字的十卷本自选集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发的时候,我和我的学生冯云香和燕红妹等,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门口巴金的那只坚实有力的文学大手。那一刻,我们的手都不约而同地伸在了大门口,和巴金大师的手紧握在了一起。坐落在北京亚运村以东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等积极倡议兴建的,受到党和政府及全国文学界的极大关注。巴金等一批著名文学家为此付出很多心血。整个文学馆的装饰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艺术氛围。馆内有国内外著名画家、雕刻家和工艺家以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品为主题精心创作的油画、壁画、彩色玻璃镶嵌画和精美的藏书票等艺术品;馆外庭院花木中,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丁玲、艾青、沈从文、朱自清、叶圣陶、赵树理等13尊真人大小的作家塑像姿态各异,栩栩如生。中国现代文学馆现有藏品30万件,很多藏品非常珍贵。目前,在新馆的展厅内,分别展出着“20世纪文学大师风采展”、“中国现当代文学展”和“作家文库展”等大型展览。这些展览从不同侧面回顾了中国文学的百年辉煌,集中展示了现代作家群体和经典作品的风貌……
步出巴金故居,漫步花园小径,只见园内绿草如茵,草坪周边白玉兰、樱花、水杉、腊梅等花木,长得生机勃勃。这些花木,大多是巴金当年亲手种植。见物如见人,我看到了花园的步道上,印刻着巴金当年和夫人萧珊的足迹,余韵漫漫。
花园葱绿的一角还安放了一个秋千,秋千旁有一个铜雕塑:表现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受难者,正张开怀抱、尽情拥抱新世纪的形象。这是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为故居揭幕仪式创作捐赠的雕塑作品。名字为“新世纪不再忧伤”。玉兰树的枝叶在铜像上轻声歌唱,沐浴阳光的铜像,似张开的双臂,竭尽全身心的力量在向天祈求,可不是吗?在特殊的年代,巴金的笔一度被禁锢了整整十二年,十二年中他只发表过一篇文章,当他能够再提起笔来的时候,他的双手已经开始颤抖,无法再能出笔似流水……然他坚持要写,他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重新握住了笔,燃起创作的热情和昔日的火焰……他用这样的干劲,用颤抖的手写完了他的《随想录》。
离开巴金故居的时候,太阳开始西斜,阳光洒在绿树和花草上,涂抹在一幢三层的洋楼上,变成了一抹红。巴金一生中创作与翻译了1300万字的作品。他永远屹立在中国文学的花苑里,成为中国文学的丰碑。
走出小楼和花园,忽然又想起了巴金的名言:“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我轻轻地一遍又一遍地念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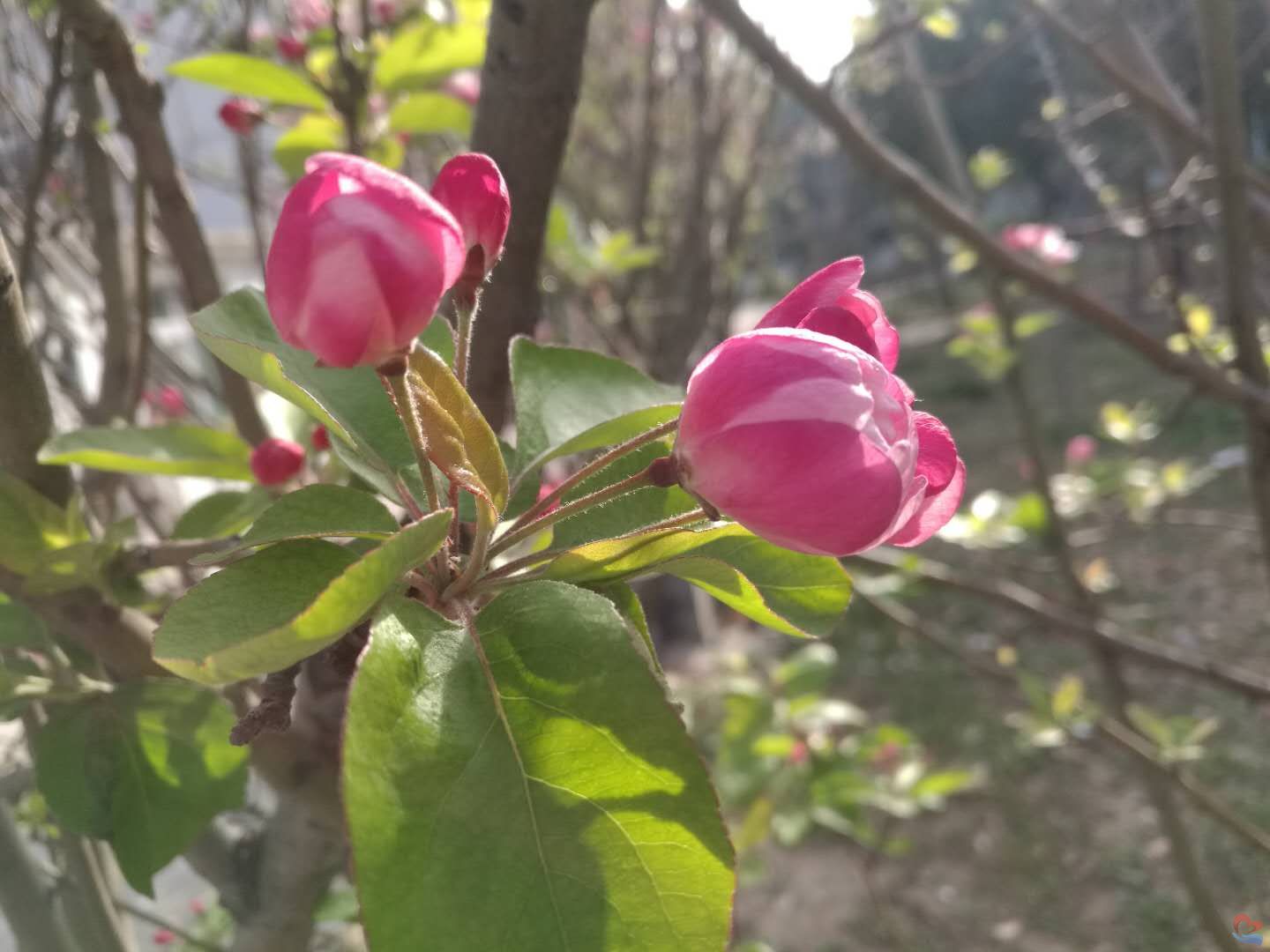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