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TOP | |||
|
漠西
管理
作者:甲申 发表时间:2015-01-09 19:38:15
评论:0条
关注
编者按: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回顾一段历史,将会对战争无比的憎恶,期求和平便会成为人们的良知。故事大致发生在大元帝国成立以前的西域,种族和部落相互征战的那个年代,涉及到了蒙古、西夏、波斯和其他弱小民族。布忽木是蒙古和西夏族的混血儿,贺兰山贫穷牧民的儿子,被蒙古人帖木儿所鄙视。不打不成交,二人成了朋友,因缴不起税赋不得不替头人去打仗。经过了生生死死的残酷战争,两个人都活了下来。八年后邂逅重逢,布忽木对战争深恶痛绝,帖木儿却为自己即将成为新头人而沾沾自喜,结果布忽木用箭射死了帖木儿,自己也用匕首刺穿了自己的心脏。故事一波三折,场面宏大,感情细腻,文笔老辣。拜读欣赏,问好作者! |
|||
|
布忽木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以躺在这渗透着沙尘的土地上,血色和污浊而干涸的泥土连在一起流向阿姆河的主干,在撒马尔罕的周围,到处可见一处处的尸体散发出来的腥臭味。布忽木已经躺在这里很久了,他站起来非常吃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破旧的刀刃散落一旁。自己的步兵甲胄被生生的划开,肉皮上的伤口已被感染成丑陋的黑褐色,像升起的大马士革上空死去的花剌子模故土上黑色的明月,这已经是这个地方和远处漠北的常态,远征军到处都是,炮火绵延在大漠的西北。 布忽木并没有死亡,身旁一动不动的冰冷的尸体上有和自己一样的梳着发辫的蒙古兵侍从和重甲骑兵战士,当然还有被杀死的穿着普通麻布和扛着木甲的波斯人,他们的脸上被血色浸染,眼神久久没有合上,一同没有合上那疲惫的沦丧家园。布忽木知道自己的族人又打了胜仗,可自己从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就没有胜利。在忽里台的大帐里面,在这个遥远的中亚细亚的阿姆河岸的大漠以西,只有死去的尸体像无人闲置的货什一样,布忽木吃力的把他们的身体一一翻好。他知道,在征服者的眼中,死去的和生着的都像蝼蚁一样微不足道,这干涸的土地也无法将他们埋葬,天空会吹走尘埃,尘埃会掩埋尸骨,尸骨下没有战刀的文明。他唯一能做的,是让每一具尸体的眼睛合上,面朝撒马尔罕城下的大漠天空,这样才能让每一个灵魂安详。 往日这里能听到阿拉伯和波斯的商队的丝绸贸易,在驼铃声声中听到东西方两岸的呼吸声。在二十多年前,花剌子模国就被族人的铁蹄沦丧,而这一次西征,在布忽木的眼神中,再也看不到大漠东方与西方的希望。当他翻过一具尸体的时候,他才怔怔的站在远处,在整个世界的中心,他嘶哑的喊破天际,仿佛被淹没在这荒原的死城岁月。这是安米提的尸体,她的脸上可见数不清的刀具的伤痕,与年轻女孩子的皮肤不同,再也没有塞种人的白色。阿古泰的身子侧在安米提的一边,他的背脊像山一样背负着几十只弓弩上射出的箭,刺穿了他的心脏和内心的家园。布忽木把他的尸体扶起,吃力的把他身上的箭矢一根根拔去,每拔去一根他都得蹒跚的倒退一米,布忽木的身体也已经无法支撑起多余的能量来了。 灰色的天空俯瞰死灰色的大地,干涸的大漠上不久传来了旭烈兀的告捷敕书,旭烈兀登上了伊利汗国的汗位。干燥的空气上弥漫着的没有羔羊,没有酒气,布忽木闻到久久的战栗味道。
(一) “夏国人的杂种。”年轻的铁失帖木儿每次经过布忽木的毡帐时,都会朝着他大声地吼。在康里部落的草原上,年轻的布忽木只是赶着牛羊,日生而作,日落而息,太阳神主宰着草原上的规律。这里谁也没有因为乞颜部首领的一次次战争给他们带来些许的荣光,在乞颜部眼里,在黄金家族的眼里,布忽木和家人只是一个留着西夏党项人血液的劣等蒙古人。 二十多年前,当成吉思汗的铁蹄踏在贺兰山的时候,势必也宣告着这个国家,这座城市与文明的彻底告别,树木上烧死了响遍兴庆府的每一句哀嚎。血流在贺兰山下,流在漠北,流尽党项人的每一寸土地。在成吉思汗倒在金帐的时候,他的苏鲁锭依然对着中兴府的居民砍去,布忽木就在一个屈辱的党项女子身上出生,她被辗转了好几个部落,直到流落到康里部落的一个普通的牧民手里。最后,他成了布忽木的父亲,而布忽木真正的父亲是谁,他从来不知道,在一次母亲凄哀的目光中,他再也没有问过。 布忽木的身子狠狠的按在铁失帖木儿的身下,拳头凶狠的对着他的脸锤去,这一次布忽木彻底把他打败,直到他从身下拔出割食羊肉的匕首时,铁失帖木儿才慌乱的语无伦次的求饶。风吹在漠北的草原上,匕首上照射出的金光反射出天空的光芒,苍鹰的鸿声撕破了苍穹的宁静。“夏国人的杂种”这句话,让帖木儿的脸上流出了一道新鲜的酒红色的血液。 这是布忽木第一次向自己的族人面前拔出了刀子,在这个年代,谁也无法预示着自己的命运。也许帖木儿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脸上永远也无法抹去的伤痕,是作为与布忽木结为安答的见证。草原上,他们向苍鹰许愿,让草原永存,让漠北的情谊见证。 那天,在草原放牧的时候,妹妹阿里海牙突然告诉布忽木在羊圈周围有不详的预兆。阿里是个出生在蒙古文化里面的女孩,是布忽木的同母妹妹,她的眼睛很大,眼神清澈得会说话。母亲看到羊羔在出生的片刻全都死去,布忽木挤着羊奶,从淡乳白色渐渐变成淡红色,羊群大批倒下,阿里海牙哭着倒在布忽木的肩上。夜色降临,族人的目光中被青帐里面的贫穷所折腾,他们必须向西迁徙。 布忽木的父亲躺在帐中不吃不喝,他的眼神像白纸一样空洞无神。老牧民的皮肤被长期曝晒成干枯的颜色,阿里海牙给父亲的嘴中喂了口稀水,父亲咕噜着喉咙,无力的嗫嚅着脸部上的肌肉,他已无力说出几句话,只是在母亲的耳边吃力的喘气。 在给父亲下葬的时候,布忽木和母亲显得很平静,只有阿里海牙的眼角在一旁抽泣。母亲的眼神中一直流露着对贺兰山的眷恋,只是布忽木看出来,母亲的眼角到现在已经没有神色,显得愈发的苍老。 贫穷和饥饿困扰着牧民的生活,哈抽剌(平民)还得为氏族的那颜们出征打仗,他们的生活变得没有依靠,当羊群和牛群尽失,没有了私有财产,连自由民都不是。那天,帖木儿给布忽木送来了湿热的肉,阿里海牙的脸上和脏泥一样,被劳顿的生活所累。布忽木把肉给了母亲和海牙,阿里海牙吃力的啃着烤的并不熟的肉,脸上有被烫伤的痕迹。布忽木问帖木儿的肉哪里来的,帖木儿的脸上流露出哀伤,居然抽泣起来,眼泪顺着伤疤的方向慢慢流淌。布忽木也许猜到,帖木儿的父亲把陪伴了自己十多年的老马宰掉分食了。老了,却是这个下场,谁都得饿死。 阿里海牙在马背上无力的吹着林布(蒙古笛),声音飘出大漠的山谷,拂过草原上每一寸肌肤。布忽木牵着马上的缰绳,目光痴痴的看着远方,看见一片黯淡的苍茫。阿里海牙停止了笛声,从马背上慢慢的跨下来,头靠在这头黑棕色的马鬃上,顺着漠北的风吹过,吹弹在她的脸上。这头老马跟着布忽木一家放了十多年的牧,是最忠实的朋友。它的干涸的眼里没有泪水,嘴上停止了吃草的举动。 “去吧,去你该去的地方吧。”布忽木重重的揣了老马的肚子。老马啸叫了一声,没有动,阿里哭了,哭动了整个草原上的风。布忽木又狠狠地踹了一脚,老马慢慢的踱着蹄声,向前奔跑,直到消失了身影。 由于交不出指定的贡赋,布忽木和帖木儿像郣斡勒一样,需要为那些贵族那颜去服兵役。在《江格尔》的长诗里面,他们丝毫没有巴特尔式的英雄主义,只是觉得草原上再也没有熟悉的声音。 夜里,升起篝火一样的窸窣声,母亲为阿里海牙梳着垂在后面的发辫,在灯火中,阿里像一个成熟的待嫁姑娘,她的脸上是干粉色的,穿着粗布的红色蒙古袍,她笑着带着泪花,挤出一个小酒窝,无法阻挡她的迷人。 “布忽木安答。”帖木儿在布忽木的毡帐外面大声的喊,毡帐已经在长期的风力中被刺破了好几个口子,有时会在睡梦中瑟瑟发抖。 布忽木看着帐里面的篝火,没有说话。 “布忽木哥哥,你还会回来吗。”阿里海牙看着布忽木,脸上没有了笑容。不久之后,布忽木将和帖木儿一起作为那颜的士兵服战争的兵役,作为义务的贵族氏族荣光。布忽木知道,血与火的金属下面,是九死一生的荒冢,没有正义。 “阿里海牙妹妹,我会回来的。”布忽木看着阿里海牙,她的脸上的妆被泪水哭花成难看的形状,“母亲,我会回来的。”布忽木看着母亲,母亲的脸和眼一样没有血色,布忽木噗通的倒在母亲的怀里,大声地哭了起来。 “我的孩子……”母亲穿着西夏的衣袍,抱着布忽木,摸着他头上的垂辫,大声地疾哭。 那天夜里,升起的篝火像神山上的火神一样,照亮了两个少年的内心。布忽木的手中握着阿里海牙妹妹的黑色的木质林布,只要想起在康里部落的草原的时候,他就会吹起这跟林布,飘荡出神山上悠扬的笛声。阿里像一个失魂的女子,她手里拿着一把掉了漆的鹰头匕首,这是布忽木送给她的,她会在毡帐中,只要注视着“它”,哥哥布忽木就会归来。因为这个鹰头的匕首上面刻有“布忽木”三个字。 “我,布忽木,帖木儿的安答。”“我,帖木儿,布忽木的安答”。在背上的木质弓弩上,布忽木把自己的一支弓箭交到帖木儿的手中,帖木儿看着布忽木,同样把自己背上的一支弓箭交到布忽木的手中,两个少年肩负着信约离开部落。如果走散了,请永远铭记安答。如果一方在战场上战死,请把那支箭安放在安答的天堂。
(二) 在遥远的漠北,水在岸边浮动。吹起羊群的欢乐的声音,一些蒙古士兵在捡拾着身边死去的公国士兵的兵器,这些是可以作为下一场战争的必要供给。 布忽木用粗布擦拭着身上的朴刀,他的手臂上是一条长长的红色印子,那是在马上,在草原上流下的鲜血。每一个蒙古兵会把这些伤口记做成为征服者巴特尔勇士的印章,可布忽木并不这样想,他会想到自己的母亲在康里部落里面的眼神,会想起阿里妹妹的哭声,会想到帖木儿安答的誓言。 布忽木疲惫的给披着甲胄的蒙古马梳洗着,它的鬃毛非常亮眼,像战士的朴刀一样,又像弯弓的利刃散出的利光。布忽木此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步兵侍从,离开部落三年,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也无法在风中聆听那一段悠扬的歌声。三年了,西征的路上何时是个头。布忽木从粗麻色的衣带中拿出林布,那是阿里海牙妹妹在自己临别的时候送给他的,林布的木头已经被摩擦的破损,但依然能吹出干净的天籁之声,听到它的歌声就能回到那一年的岁月,那一群牛羊在草原,无忧无虑。 他在笛声中睡着,靠在那匹蹲着的马上。在梦乡,漠北的乡泽之水非常清澈,漠北的夏天,在清泠的风声中非常干净。布忽木笑了,在梦中笑了,直到被一声凶悍的斥声吵醒。 这是一个普通的军阶士官,履行管理马厩的义务,他满脸的络腮胡子,头上是一个“三搭头”的发辫。在他的眼里,只要是比他小的士兵,他可以随意的呵斥,可是马背上的骑兵和巡检司以上,他就喜欢弓着背了。 “你,快给我站起来。”“三搭头”挥舞着马鞭,重重的打在布忽木的身上,透过麻布,里面可以看到清晰的红色的印子,像一条鲜红的沟壑。布忽木快速的站起来,向前的草原奔跑。 草原上正在进行蒙古搏克,他们穿着更加破旧不堪的粗布,足以遮住一点点身体。那些巴依勒德(摔跤手)目光凝峻,他们明白,每一次必须要将对方打死,才能把生存留给自己。夜色越来越凝重,大会上开始萨满教的舞蹈,非常壮烈。篝火燃起雄壮的马背上的力量,那颜在榻坐上大声的笑着,他的脸是青色的,耳朵上闪着一边的铜光,像一把利剑刺向对方。他高声的拍着手,“三搭头”士官踉跄的弓着背递着清酒,那颜痛快的饮干,像啮噬掉羔羊的最后一块肉一样。他习惯性的把一只脚挂在“三搭头”的肩上。 “你说,他们谁会赢。”那颜醉醺醺的指着搏克场上的两个奴隶,这些奴隶是战败的公国俘虏,他们费劲力气纠缠在一起,身体上缠绕着彼此的器官企图把对方杀死。这边,那颜和他的贵族们披着裘皮,快心的大笑。 “尊敬的那颜先生,您是草原上的主宰,你赐予谁的胜利,就是谁的荣光。”“三搭头”至始至终没有抬起头,喘着气说道,一边的巫教舞蹈把篝火升起一团鹰头的形状。 “哈哈哈哈……”那颜笑得非常满意,喝干净坛子里面的清酒,随手往后砸到地上,“嘭——”清脆的声音在嘈杂的格斗与舞蹈面前也能震慑出一道鲜亮的光芒,像撕碎黑夜一样。“好——”他大声的鼓掌,看见一个俘虏被另一个俘虏掐死在搏克场上,接着又笑着捋着胡子和发辫高兴的侧坐在榻座上,顺势把脚继续勾在“三搭头”的另一个肩上。他们把尸体丢弃在一旁的坑里面,上面堆起的身子已经隆起到地面以上,草原上的水有一股腥臭的难闻的味道。布忽木的内心又因为自己的一丝丝怜悯而产生反胃的状态,周围的蒙古士兵和步兵侍从以及底层士官都挥舞着复合弓和蒙古弯刀,高亢的喊叫冲破了漠北向漠西的天际。此刻,出征向西,塞北高原上的雪水也融化不了战士的心,布忽木的内心没有一丝草原上战士的荣光。 “我的武士……”那颜高兴的抚摸着“三搭头”上的那一撮稀松的头发,像抚摸着温顺的狮子一样,“我亲爱的武士,你可以战胜那个高傲的奴隶吗。”那边,胜利的巴依勒德奴隶将倒下在一旁的鲜血擦在自己的身体上,身体上散发着男性的自然气息,让人不寒而栗。 “我亲爱的那颜先生,我是你忠实的奴仆,是你最温顺的家人,我的职责……”“三搭头”停止了说话,他不敢看着那颜奴隶主的眼神,那颜收敛了刚才的笑容,露出凶悍的要杀人的光芒,一声拔出驽钝的声音闪过,割开了大地的号角。 “哈哈哈……”那颜突然又大笑了起来,抚摸着“三搭头”的发抖的头发,“你是我忠实的奴仆,哈哈哈……” “呵呵呵……”“三搭头”顺着那颜的笑声附和地笑,非常不自然,他的声音在战栗。 “滚!”那颜的脚从他的肩上迅速的抬下来,飞起一脚踢在“三搭头”的肚子上,他踉跄了好几米远。 “是……滚,滚,哈哈哈。”“三搭头”低着头,看着那颜和贵族们,他难看的挤出脸上的笑容,又大声笑了起来,肮脏的身体上的盔布从地上到另一个地上,他顺势从地上爬起,横着往下滚去。 “哈哈哈——”那颜和蒙古贵族们的笑声在篝火中越烧越旺。 在马厩里面,布忽木除了负责照看披着甲胄的蒙古战马以外,还得看管郣斡勒,郣斡勒是“奴隶”的意思,这个被俘虏的塞种士兵遍体鳞伤,血从刚结了痂的伤口上又不规则地从不同的方向流出,他的伤口是被“三搭头”在愤怒的解气时吊在树桩上抽打的。郣斡勒叫什么名字,谁也不知道,只被叫做“郣斡勒”的塞种男子刚从搏克赛场幸存下来,还得服繁重的劳役,被士兵看管,被“三搭头”的马鞭抽打。 布忽木看着他,郣斡勒是个彪悍的白肤汉子,会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在阳光的曝晒下是特有的牧民的古铜色的肌肤,只是魁梧的肌体上是遍体的伤口。布忽木和郣斡勒是马厩里面唯一的朋友,他没有因为自己蒙古士兵的身份而高傲,在空旷的营寨里面,自己也是西征路途上疲倦奔跑的战马,直到累死也不会被怜惜。 “郣斡勒。”布忽木拉开木门,发出难听的破擦木屑的声音,一丛光线照到草料上,郣斡勒警觉的用粗糙的单手遮盖眼角,又本能从一只手中拿起一旁闲置的铁器。 “是我。”看到布忽木的脸,郣斡勒才从警觉的神经中松懈下来。 布忽木把涂伤口的草药敷在郣斡勒的手臂上,肩上,后背还有脸上。郣斡勒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的摇摇晃晃,终于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我去给你倒水。”布忽木说,把刀具放在一边。 郣斡勒在喝完水以后,眼睛出现迷糊的景象,他开始疲倦的睡着了。天边传来牧歌,是从遥远的大漠吹来,那些久远的部落里面的故事,还有年轻姑娘的舞蹈。在青色的绿洲上,踏马归来,有轻快的驼铃声声,最熟悉不过的了…… “你在吹什么。”郣斡勒从睡梦中苏醒,伤口还是一阵升腾,他身边的枷锁已经打开。布忽木在一旁吹着忧伤的林布,这个时候在遥远的西北,他又想起故乡的草原上的牧民和自己的家人。 “这是我的亲人,我的安答……”布忽木放下林布,疲倦中的天籁瞬间停止,“郣斡勒,你想念你在漠北的亲人吗。” “我?哈哈哈,我已经没有了亲人。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妻儿,都在你们战士的屠刀下失去了,我们的田园,我不再想念天边的牧歌。”郣斡勒停止了说话,抽泣了起来。布忽木很难想象一个魁梧的男子脸上的流下了最清澈的眼泪,像天山上的雪水一样。 “我有一个美丽的妻子,他的眼睛像画中的仙子,我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他的眼神像海岸上最纯净的诗人,可是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不再存在……”郣斡勒说话语无伦次。 时间像停止了一样,马啸从圈中开始大批的出现。布忽木仓皇起身,把草料迅速的放进马圈里面。 布忽木走进马厩里面的看房,刚吃力的坐下,就被郣斡勒一把抓住无法动弹。“听着,今天你得让我逃离这个营帐。” “这里到处都有士兵看管,谁也无法走出去,我们都无法活着出去。”布忽木无奈的说,身体一直被郣斡勒有力的拽着。 “听着,今天晚上,趁那个秃子睡着的时候,我们必须悄悄的逃出去。我不能死在这里,如果你愿意逃离的话,可以和我一起逃走,就在今天,你没得选择。”郣斡勒说着,钝刀已经架在布忽木的脖子上,有一道血印子。布忽木想着远在东边的漠北的草原,漫长的西征的路途,他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是他会非常想念自己的母亲,还有妹妹阿里海牙。风吹在营寨上,吹熄了一团篝火,变得非常安静。 夜里,篝火被点亮,士兵却非常停止地站着最后一班岗。马厩上的战马疲倦的趴着,不再进食。布忽木示意郣斡勒从马厩的后面迂回,先躲在草料的后面,再见机行事。今天晚上,布忽木也打算逃走,他讨厌这里的气氛。 “快,郣斡勒。”布忽木提醒了他,自己轻声地跑在前面,他们俩已经走出了营寨四米,布忽木开始提着步子向前快步跑了起来。 一声马叫打破了宁静,也把郣斡勒绊倒在马蹄边上,他的身体从上到下重新种种的撞击在泥土上,无法再爬起来。蒙古侍从“三搭头”已从听到的动静中快速的跟进,“快跑,布忽木。”布忽木试图回过头,被郣斡勒的声音制止。 “三搭头”像发了疯一样地挥舞着弯月一样的蒙古刀,他在向下一次的战功疯狂的奔去。 “快跑!”郣斡勒厉声朝着他大喊,布忽木不再回头,向前跑去,他希望跑到不再遇到军营的地方去,不再到西征的路途上去,那里有清水,有草原,有羊群。布忽木仿佛听到后面清脆的声音,后背一阵发凉。郣斡勒的头颅在沾染着血的朴刀下倒下,在风中坠落。 那天晚上,布忽木跑得很远,他的面前已经没有方向,只知道未来的天空上没有苍鹰飞过,像被浸染了黑色的血变得异常浓重,大漠上有蝙蝠飞过。布忽木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睡着,在睡梦中只知道自己在想起漠北草原上的事情。 早上醒来,布忽木的眼前是一片黑色。在自己的一段挣扎中,他知道自己被装在一个厚厚的麻袋中被几个人驮着。他依稀听到自己族人磨刀的声音,和奴隶主那颜差不多的话语,他的眼前是数不清的无尽黑色,也许这一刻他想到自己的头颅被安葬在这个未知的大漠的西边。 布忽木并没有被杀死,双手被捆在一匹马的缰绳上被牵引着,随着马在行军路上的奔跑,草原上的枯萎的草被自己的身体刮起一地飞尘,前面是一片戏耍的欢笑声。布忽木知道自己的噩梦刚刚开始,他被士兵牵着走向更加往西的方向。随着乃马真后的在忽里台发出的西征命令,旭烈兀开始了在马背上往黑衣大食的西征路程,布忽木被逮到另一个营帐,继续着往另一支军队的西行。 他随军队驻扎在恒河之上,布忽木离漠北越来越远,林布已经从自己的衣带中消失,矗立在漠北的草原和大漠一起风化,也许从那一天开始,他的身上的缰绳开始彻底的沾上了死人的血,他再也听不到边塞的牧歌。
(三) “你们知道,你们是乞颜部最高贵的子孙,你们要为自己流下的汗与血付出一切。你们的妻儿在金帐中举起白色的奶酒,跳起大舞,让我们攻下这座城池,成为百户,千户,万户……我们的母亲是高贵的,是飞翔在蓝天上的雄鹰的女儿,让我们为了母亲在金杖面前的守候做最后的冲杀吧!”也许连布忽木自己都没有想到,在这座十八年前被铁木真汗攻下的花剌子模的国家里面,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重甲骑兵的统帅来决定着这座城市遗民的生死。当西征的蒙古士兵挥舞着大刀的时候,五年后的布忽木已经习惯了在战场上流血的一切。 战马纷纷倒下,扎兰丁苏丹死后的木剌伊国的骆驼被沙尘中的马刺与马钉深深刺穿,他们倒在了撒马尔罕的城下,这里没有草原,这里是干燥的绿洲上的泥墙,轰然倒塌。 “帕勒吉(干杯)。”营帐里面,布忽木目光冷峻,目视着底下静坐的穿着铜甲的骑兵,大声的吼道。这一次,他又攻克了西征路上的一座城邦。 “帕勒吉——”将士们一饮而尽,把空酒坛纷纷打落地上,迸发出强烈的光芒。军帐上屹立的铜铖的利刃刺向一旁的士兵,布忽木毫不怜惜的将俘虏的尸体踢到一边,金帐中响起了巫歌与可怕的豪迈呐喊。 马蹄声踏在过去骆驼步行过的泥尘,马刺在地上钩出一道道血红的长辙。布忽木的行军战马走在正中的前方,手中的弯刀在阳光下折射出杀人的影子,让燥热的空气一下子变得寒冷而肃杀。 狼烟四起,号角空沉,把死亡与生存的地平线压倒最低处。战马嘶叫,刮起了烈烈而干涸的雄风,对面的士兵缺盔少甲,多是游散的兵勇。蒙古马在大地上咆哮,金光划破了天际,掩埋在一片厮杀里面。布忽木的眼睛被一处红光覆盖,他的胳膊被巨大的力量压住,感到失去了重心,重重的从马背上摔下。 这一次,布忽木的西征军输得非常彻底,而他,也在这一次马背上失去知觉。 天色非常昏暗,太阳被撒马尔罕的天空覆盖。布忽木吃力的睁开眼睛,却被额头上和身体上的一道道伤口刺得生疼。他的眼睛旁边是血红色的伤口,顺着眼颊,红色的血慢慢流下,他的蒙古骑兵头甲已经挂在对面的营寨面前,而他一动不动,身体被捆缚在木质的十字架上,无法挣脱。 撒马尔罕的阴翳的白天,已经被黑色笼罩。布忽木的脚下面是一团团的篝火,他们涂着黑彩在跣足翩跹,这是波斯的拜火教的舞蹈,布忽木仰望着撒马尔罕天空上的日食,哀伤的叹息自己的死亡祭祀。 冷风吹熄了布忽木耳垂边的两团细火,这是他五年行军生涯的第一次彻底的恐惧,恐惧蔓延他的全身,蔓延在天空被无尽的黑色吞噬。 一把利刃在他身上划过,布忽木的双目紧闭,变得非常安详。他从十字架上面疲软的滑下,布忽木发现自己并没有死,只是绳子被道具刺开而已。 “住手——”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是尖锐而有力量的,这时从布忽木的眼前是一个戴着高耸圆顶的蓝色礼拜帽的女子,她叫安米提,是萨珊酋长的女儿,黑色的头发和细长的睫毛是亚述人特有的美丽。她的手指一处有一处疤痕,布忽木非常清楚的明白战场上的一切。 “阿古泰——”安米提喊了一声,声音刺穿黑色的太阳。布忽木听不懂波斯语,对未知的害怕,面前的高壮的亚述男子阿古泰走在布忽木的面前,一把揪住他的疲态的布满伤口的身子,布忽木臂膀左边是一支利箭的伤口,正是这支中亚战场上的箭,让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布忽木被阿古泰抬着,他不知道接下来可怕的死亡要怎么面对。 在任何一场非正义的征服者的疆场,敌人与自己都要面对着对失去一切的死亡的祈祷。大漠以西的天空上,太阳依旧是金色,一切恢复正常。而布忽木却从陌生的营帐中醒来,一切也都安好。 他试图从地毯上起来,身上的甲胄已经不见,肩上的伤口还是疼得让人死去活来。阿古泰从布忽木的眼前出现,阿古泰的脸上始终是冷傲的表情,白肤色和他冰霜的脸一样。阿古泰的手上是一把特制的波斯铜剑,从他裸露的孔武有力的肩膀上可以看出,阿古泰是个死士。 阿古泰弓着身子,从他的侧边是清澈眼神的安米提,她穿着普通的蓝色绸布,依然无法抵挡她的高贵。布忽木明白阿古泰是安米提的贴身侍从,而自己却不知会面临什么。 安米提从一个侍官旁边接过铜色的细杯,递到布忽木的面前,布忽木的蒙古辫发已经松散成一绺绺的髠发,他无力去打理它。布忽木看着安米提的纤细而带有粗茧的手,杯子里面是什么,布忽木在他们的波斯语中狐疑的一饮而尽。 “你受伤了。”安米提微笑着说,“我让阿古泰来照顾你,他是很好的将士。”布忽木怔怔看着安米提,他听不懂安米提的波斯语,但揣测中明白,安米提并没有敌意。布忽木看着阿古泰,这个像石块一样冷峻的男人一动不动。 西征军队的最高统领旭烈兀和蒙哥以及另一支在西北的统领长子拔都发动了对窝阔台帝国的又一次内战,他们为了自己的新一轮汗位而战,蒙古人的血又一次流向自己的族人。而此时,大漠以西的驻军面前的太阳出现了新一轮的和平局面,在撒马尔罕的干燥空气下,有印度洋的季风吹过,久违的雨水落在城下。 布忽木把自己的髠发结成圆状,像波斯人一样。安米提冲着他笑着,布忽木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个营帐里面等待新生,而他也无法面对在大漠以西的士兵和将士。 夜晚,月色像迷人的猫的眼睛,是会说话的。行帐里面是起舞的声音和打击的鼓声,布忽木慢慢的走出行帐,看见安米提舞动着像水蛇一样的细腰,军士们在火把的助威声中举起红色的酒液,漫步着舞姿,在波斯的清乐声中,他们忘我的庆祝着。 布忽木看得出来,这是摩尼教特殊的节日,在行军途中,他至少知道一些在亚美尼亚当地的风俗。布忽木轻声的走了过去,就被安米提拉倒自己的身边,在音韵的作用下,布忽木挑着别扭的舞姿,和他们开心的笑着。顺着手抱在安米提的腰上,有一股亚述人特有的麝香的味道。 在一股特殊的力量之下,布忽木被推倒在火把的一边三米之外,阿古泰的眼神像夜鹰一样,拔出利刀,面向自己。布忽木知道,阿古泰不仅仅是安米提这个美丽波斯少女侍从那么简单,火盆在布忽木的一旁散落,里面的热碳灼伤了他的手臂。 “阿古泰——”安米提朝着阿古泰怒吼,这个高大的冷峻波斯人瞬间停止了冲动的举止,只是目光一直盯着布忽木,恨不得吃了他。 深邃的夜,布忽木被一股清悦的乐声走出梦乡,在异域的城邦,他头一次在战场以外能听到天籁之音。布忽木曾在一个阿拉伯的商铺看见匠人的手工乐坊,在战争里面,音乐沦为了屠刀下的奴隶。这是特有的波斯兰笛的声音,布忽木朝着声音缓缓走出。 她的后背在风声中是曼妙的,发丝被皎洁的月光照射出浓郁的金黑色,安米提独自在行帐外面吹奏自己的哀伤。布忽木走了过去,没有发出声响。安米提停止了笛声,看来她发现了布忽木的到来。 “安米提”布忽木用生硬的波斯语说,接着话噎在喉咙里面,没有继续说下去。 “你怎么了,布忽木。”安米提说,眼睛看着撒马尔罕天空上的月亮。 布忽木也看着天空,上面是斑斓的星,那是一缕缕的思念。他抬头吹着林布,和着清风中的思念,把音符吹向远方。 “这是什么,真好听。”安米提看着布忽木,天真的笑着说。这是布忽木在西征途中找到一个阿拉伯的匠人制作的林布,远在漠北,他无法回忆起妹妹阿里海牙的那根蒙古笛,林布里面的声音再也没有西征岁月里面的杀戮,静下来聆听,是漠北的羊群,在遥远的漠西,什么思念都随风散去。 布忽木苦笑了一下,没有继续说下去。 “这是什么。”安米提夺过布忽木手上的林布,指着上面纹着的蒙古文字。 “那科尔,是朋友的意思。”布忽木说。 “那科尔。”安米提重复了一下,看着布忽木,笑着。 “那科尔。” 第二天的清晨,第一粒阳光洒在新生的绿草上,它是死去的枯草上面新生。安米提手里拿着布忽木送给她的林布,她知道,布忽木必须要离开。 “不行,安米提。他是蒙古人,不能让他走……”波斯的族人看着布忽木,詈声的看着安米提,朝着布忽木吼道。 安米提用萨珊酋长的旨意停止了他们的争吵,她慢慢的走到布忽木的面前,朴素的衣料上面是她高贵的心。安米提把那支波斯兰笛放在布忽木的手上,“希望我们还能像这样见面。”安米提说。 布忽木没有听懂这句波斯语言,只是他的手心是热的。他也许知道,蒙古与波斯之间再也没有战争,至少他不会再披上甲胄。他和阿古泰做了一个拥抱,阿古泰的手臂宽阔而有力量,他的嘴角扬起一个小小的酒窝。他惊奇的发现这个冷傲的男子也是会笑的。 布忽木手中的波斯兰笛,上面纹了蒙古文字,布忽木知道是安米提纹上去的,是“那科尔”,是朋友。
(四) 布忽木牵着瘦马,提着蒙古刀,又把刀放在马背上,穿着商人的衣服,步行在撒马尔罕的城下。在大漠的西边,霞光是一轮残缺的美丽。商铺上面是疲倦的商人,他们要继续繁重的税赋和步履维艰的生活,除了蒙古人,还要遭受野蛮的色目长官的无条件的欺压。 这片干燥的土地里面,有布忽木曾经屠刀下的鲜血,已经被时间风干。但是布忽木的内心永远无法把它忘却。 大食国的城邦里面,阿拉伯商人躺在一旁,骆驼的呻吟声渐渐微弱。泥墙上边有族人的哭泣,他们在祈求先知的福音。在包头巾的头箍上面,每天的重复像地上抓起的一抔黄土一样干黄。 一个女子在一个死去的男子身旁幽泣,穿着绸布的色目回回巡检司在一旁拿着朴刀一动不动,这是死城下的常态。转让奴隶更是每天发生的事情,掩盖尸体走向天堂也是每天的必经之路,布忽木知道,即使旭烈兀的缰绳不再这里,士兵与武士依然驻扎着每一把屠刀砍向无法反抗的居民。 在蒙古的长诗里面,都是歌颂英雄的赞歌,小人物在地上匍匐也画不成一个生命的符号。布忽木想到这里,又看着身边的瘦马,已经快要老死的瘦马,他再也没有骑到它的背上。他牵着它,与它一起平视着前方。 布忽木面前的女子,看上去只有十八岁左右的样子,在干燥的空气中她的面容并不姣好。手上留着痂血,布忽木看到她身旁的男子是上顶秃头的髠发,这是西夏男子的特有发型,只是他们并没有穿着属于自己族人的衣服,这个男子或许是女子的父亲,哥哥,还是丈夫,布忽木并不知道。但布忽木心中怜起一股忧伤,他根本想象不出夏国人的家园是怎样的,母亲告诉布忽木,那是贺兰山的火海,族人再也无法再此安眠。 “姑娘,他已经死了。”布忽木叹息着,走到她的身边,看到女孩的眼角上有一层清晰的泪膜。 “滚开,她是我奴仆,你没权在我这里站着。”一个说话豹声的回回巡检司挡在布忽木的面前,一脸横肉,嘴唇上挂着两撮搞笑的八字胡,“她的命运有我主宰。” “天哪,我们谁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我们都有生存的权利,何况他的死亡和我内心的怜悯,难道你没有怜悯之心吗……” “好了,我的大人。可是这个时候,谁也无能为力,除非你能出更多的价钱,这样你才能主宰你的怜悯之心。我的大人……”巡检司笑着,难看的脸上的肉随着让人憎恶的笑声往下下坠。 布忽木看着女子的眼神,又抚摸着身边老马身上的鬃毛。“好吧,多少钱,你说。” “五十锭。”巡检司的喉咙里发出难听的豹声。 布忽木看着老马的眼睛,又苦笑着看着巡检司嘴上翘起的胡子。这可是比买这匹垂垂老矣的老马还要便宜的价钱。布忽木从自己的衣袍中拿出40锭波斯币,戏谑的笑着看着巡检司的脸。 “还差十锭。”巡检司摸着上沿的胡子,不依不饶。 布忽木从马背上取下他的蒙古刀,上面裹着一层茶色的布。抽出纹着鹰隼图案的刀柄,发出清亮的响声在光线的折射下发出刺眼的银光。可是,再好看的刀柄,再好看的刀具也是流着别人的血液,他们在看不见自己亲人的遥远的面前死去。 “拿走吧,它值十锭。”布忽木不屑的说,说完就拉起这个一脸惊愕的西夏女子,把死去的男子放在马背上,老马每走一步都在喘气。巡检司捋着上唇的胡子,反复的看着刀柄和刀身上的纹路,他深感大赚了一笔,这刀起码值八十锭。 女子把死去的男子的身体放在一处长满草的土地上。布忽木后来知道,这是女子的哥哥,在贫穷与战乱中,在恶毒的巡检司的抽打中死去。女子来不及哭泣,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厄运还会继续,转卖奴隶在战争与饥饿中无法离去。 布忽木替女子的哥哥安葬好以后,在一处荒弃的房子里面暂住了下来,里面有破旧的弓弩和炊具,看样子主人出征在外很久没有回来了。 外面有些起风,漠西的绿洲草地上开始变冷。布忽木把自己的宽袍披在女子的身上,她怯怯地往后退去,在这个蒙古男人面前,她无法不害怕。 布忽木看着她,眼睛里面有一丝酸楚。“你叫什么名字。”布忽木迟疑了一下,用党项语对女孩说。 “细封都兰。”女子小声的说。 “都兰,它是贺兰神山上的一种仙草吗。”布忽木看着细封都兰说。 “是的。”细封都兰回应他。 “除了你哥哥,你的家人呢。”布忽木继续对她说,点燃了地上的一团野火,开始出现噼里啪啦的声音,火星开始迸了出来。 “我的家人,他们早就已经不再了,他们死在了蒙古人的屠刀下。我是夏国人,可我从出生起就不知道我的故国是什么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贺兰山。”细封都兰的眼睛非常空洞。 “我也一样,那荒芜的家园。”布忽木把一根废弃的木材丢进火堆里面,目光对应着温暖的火焰。 “你是夏国人?你会说党项语。”女孩对着布忽木说,把手伸到火堆旁边,透着火光能清楚的看出她皮肤上斑驳的伤口。细封都兰已经不像刚才那样怕布忽木了。 “我……我是夏国人的儿子,可我却拿着蒙古人的屠刀。”布忽木目光变得冷峻起来,在戴月的星斗里面,他看不清漠北的边缘。细封都兰看着他,也没有说话了。 “你知道吗?曾经有个人叫我‘夏国人的杂种’。”布忽木无比戏谑的嘲笑着自己。 “那后来呢?”细封都兰马上问道,她很有兴趣听下去。 “后来我狠狠把拳头打在他的脸上,并用刀口在他的脸上划开一个永久的伤口。”细封都兰看见布忽木的眼神,跟火光一样带着愤怒了。她没有再问下去,也没有继续听下去。 “我有在草原上的母亲,她是党项人。党项人的家园和我的草原已经不再了,我的妹妹也许已经出嫁了,成了一个母亲。我知道,每年我们都会依水迁徙,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居所,在毡房里面,我们可以吹起林布,听天边的牧歌。可是,现在,我与他们失散了,彻底的失散了……”布忽木突然喝起来酒,独自说着。 夜色被屋子里面的火光充盈着唯一的温暖,布忽木靠在木堆旁。细封都兰只是坐在地上,她的裙子变得很脏。在她的衣带中,有一个金属的玩什,已经失去了光泽,是一个短头的鹰头匕首,布忽木一把夺在自己身边,他清晰的看到刀具上面已经模糊掉的“布忽木”的三个字。 “这把匕首,怎么在你手上。”布忽木眼睛瞪着细封都兰,一动不动。 “是我哥哥,他送给我的。”细封都兰看着他,开始害怕的细声地说。 “你的哥哥呢?”布忽木继续追问。 “他已经死了。”细封都兰身子开始后退,眼睛开始出现泪水,声音和哭声一起变得呜咽起来。 布忽木才从暴戾中走出来,开始让自己变得平静。他仔细的看着匕首许久,又对着她的目光盯着许久。“你是阿里海牙,是阿里海牙妹妹,对不对。”布忽木把眼睛睁大,看着细封都兰的眼睛。细封都兰却被布忽木拽住胳膊,一次次的恐惧。 “不是,不是,我是细封都兰,我是细封都兰。”她哭着,不停地说。 “快告诉我,我是你的哥哥,我是你的哥哥,我是在康里部落的布忽木哥哥……” “不,不,你不要再逼我说了。我的哥哥不是蒙古人,我的哥哥是夏国人。”细封都兰终于把布忽木的手挣开,开始往墙角靠去。 “你的母亲呢?”布忽木对细封都兰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问。看着她怯怯的发抖的神色,布忽木明白。“她,死了。对吗?”布忽木目光像白纸一样。细封都兰看着他的目光,她垂下的发辫像一绺绺的绝望埋葬在异国他乡。 布忽木终于镇定下来,他抚摸着自己蒙古人特有的发辫,还有战刀。布忽木在清楚的明白,自己只是夏国人的杂种。他的屠刀和鲜血,让自己永远的离开家园,他再也回不去漠北。 “母亲——,阿里妹妹——”布忽木朝着天空大喊,只有回声。这里,与遥远的世界彻底的失散了。 细封都兰在夜的篝火边已经合上了眼,布忽木抱着匕首一直没有合眼。外面的马开始不知疲倦的嘶叫,有士兵巡夜的声音传来。 天开始变亮,野火堆上的木材已经成为了木炭。布忽木去牵老马,却发现细封都兰已经不见。布忽木迷惘的望着远方,有一只麋鹿奔跑而过。“细封都兰——”他大声地朝天上喊,回声震落到自己的耳膜,一切依旧。 在飘荡的泽水边上,布忽木为老马梳洗着身上的一切。他发现细封都兰的后背朝天漂浮在水上,血和水一起融化,她的后背上有许多支弓箭,刺穿了她的心脏。
(五) 布忽木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再一次出现在行军的营帐。随着细封都兰的死去,他在茫然的草地上被驻军的蒙古士兵俘虏。也许这一刻,布忽木明白自己重燃的心又像灰一样,死去。这次他没有了骑兵统帅的身份,而是被编入了步兵侍从的队伍。他疲倦了这撒马尔罕的土地上的被马蹄扬起的一切尘土的气味,他渴望听到这里亲切的驼铃的声音。 他再也不想披上甲胄,如果当时间可以倒退到漠北的时候,他想永远的安居部落,不再远走。可是,一切都无法改变,当他的身体和衣服被血肉模糊,疲乏的站在撒马尔罕的城下,看着安米提和他们族人的尸体的时候,他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布忽木的恸哭像狼的嚎叫撕破了天际,他无法相信这一切。 布忽木亲眼看着细封都兰的尸体沾染着自己族人的血,安米提和阿古泰的血再一次让他瘫坐在地上。他翻着一具具的尸体,祈求上苍给予他们的重生。阿古泰的身体僵硬的被无数条弓箭刺穿,他想象的到他在生命一刻安守在安米提面前的勇敢的胸膛,布忽木已经忘记了这个魁梧男人的冷峻与高傲,他只记得阿古泰的那一抹微笑。当他们为自己的波斯的家园而浴血的时候,布忽木知道自己有多么的让自己憎恶。 如果不是藏在胸袋的那支波斯兰笛,布忽木也许就被弓箭射穿在撒马尔罕的土地上。这支纹着蒙古文字“那科尔”的波斯兰笛,不能再吹出美妙的声音,它飘不出山谷,也穿不过河流。布忽木把它放在阿米提的身边,让她永远的安眠。 尸体上堆积的血像汇聚的一条条河流,流入了干燥的土地。布忽木现在看到腥红的颜色就会一阵眩晕和重影,他的身体会不自觉的前后摇摆,他被一股力量推倒在前面。 “大帅,我看到他在波斯人的身边。他是细作,是我们族人的耻辱。”布忽木才知道自己的身体再一次被捆绑,他被逮到一处行军的营帐里面,迎头的是血光下滴着鲜血的战刀和披着甲胄的骑兵。 布忽木一动不动,他已经没有了对生存的一点点思忖。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波斯人的地方。”面前的将军是一张冰一样的脸,脸上有被塞外的风刮过的痕迹,眼神被犀利而又冷傲的目光充斥,他的左脸上有一道深色的疤痕,长长的,看样子已经是好几年遗留下来的疤痕。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敌人的地方。”将军又一次呵斥了布忽木,而布忽木只是默默的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他不想再想什么。 “快说,我们大帅问你呢。”侍从把跪在地上的布忽木再一次踢到在身子左侧,布忽木只觉得身体的眩晕,很难支撑起爬起来的力量。 将军示意侍从走开,而是一改刚才常态的面容,他笑着拔出蒙古刀,在布忽木的面前晃悠。“说吧,你叫什么。” 空气是被凝滞的,布忽木知道下一秒自己的脖颈就会顺着血液流下的方向,慢慢的坠落而死去。“布忽木,我叫布忽木。” “布忽木?”面前的将军突然收起刀刃,惊讶的看着他的脸孔,“是那个在漠北的康里部落的布忽木吗?” “是的,将军。”布忽木大声的说。 “布忽木,你看看我是谁,你不认得我了吗?”面前的将军突然脱掉头上的盔帽,是一个“三搭头”的发辫,“我是你的安答,铁失帖木儿啊!”将军一改刚才的态度,面带惊讶与微笑,双手扶在布忽木的双臂上,仔仔细细地看着布忽木。 “你是帖木儿安答?”布忽木看着面前的脸上带疤的蒙古将军,“你真是帖木儿安答。”布忽木突然喜出望外,八年的时间,居然在漠西的营帐相见。 “混蛋,快给我的安答松绑。”帖木儿朝着身旁的士兵大声的吼叫,像训斥一匹马一样。他把朴刀和蒙古刀丢在一旁,很布忽木拥抱在一起。 营帐外面是干枯的草地,绿洲上面的水源已经变得肮脏。“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我的安答。”帖木儿坐在自己私人的毡房,举起奶酒,对着布忽木开心的笑着。 “是啊,真没想到。”布忽木却苦笑着。 “我的安答,要不是你,我们也不会找到波斯的营寨。你将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步兵侍从了,我要向大汗请示,让你拥有一个大帐的帅印。”帖木儿大声的说,“因为你是我的安答。”帖木儿把手放在布忽木的手上。“我,铁失帖木儿。布忽木的安答,让大漠的苍鹰铭记,永生永死。”布忽木看着他脸上的伤疤,却笑着没有说话。 “帖木儿,你总共攻克了多少城池,征服了多少土地。”面对眼前的指挥使,布忽木知道杀戮是邀请战功的可怕力量,让他不寒而栗。 “不,不,我的安答。我们是大汗的子民,我们是草原上的雄鹰,我们不在乎多少人的鲜血,我们是征服者。知道吗,我们顺从蒙哥汗,旭烈兀汗的旨意。”说完,帖木儿把手上的大碗奶酒一饮而尽。 “你可知道,我的安答。”布忽木停顿了一下,“我们的哈达不再是白色。” “那是什么颜色?”帖木儿笑着吃惊的问。 “红色。”布忽木认真的说。 “哦,我的安答,你应该是天主或者吟游诗人。可惜,这是战场上的一切。”帖木儿收敛笑容,“看吧,我外面的一切,士兵是我的侍从,这片土地是我的庄园,这片大漠和绿洲是我的无尽的宝藏。”帖木儿拉开营帐,用手指指向外面。 “是的,指挥使大人。”布忽木垂下头说。 士兵的铁器声音打击在一张张被屠宰的马皮和骆驼肉上,布忽木看着,心仿佛被一次次刺痛。“帖木儿指挥使大人,我想在你的营帐外面走走。” “安答,请披上它吧。”帖木儿拿出一张骑兵的甲胄,示意布忽木穿上。 “不,我穿着这些,它就驮不动我了。”布忽木抚摸着身边的这匹老马上面的鬃毛,看着帖木儿说。帖木儿一脸失望的拿着兵甲,戏谑的笑了笑,没有说话。 帖木儿穿着引以为傲的将军兵甲,骑行在布忽木的前面,凶悍地挥舞着马鞭:“看吧,我的安答,这里都是我的土地。”他回过头自豪的看着布忽木,缰绳把马头紧紧箍住。 “这里不是我的土地,我的家园在漠北。”布忽木闭着眼,无力地回答。 “我的安答,这里你想拥有什么就有什么。女人,波斯女人,大食女人,马皮,骆驼,士兵,还有可以使唤的奴隶。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让自己自豪。”帖木儿说,“在那个遥远的漠北,已经是取代贵由大汗的蒙哥汗的土地,我们在旭烈兀的汗国里面,也可以行使着我们的苏鲁锭的权力,不是更好吗。” 布忽木任由他的发辫被风吹过,沙尘依附在他的头上,发辫上和衣服上。 “二十年前的这里,不再有花剌子模的苏丹,现在不再有波斯的王,马上也不再有大食的君主,这里只有我们的大汗,只有我们是这儿的主宰。”帖木儿面向长空,张开双臂,大声的疾呼。 “帖木儿。”布忽木看着他,沉思着,“你还记得我们的誓言吗。” “当然记得。”帖木儿低下头,严肃的看着他,从自己的后背弓袋中拿出一支八年前的破损不堪的铁头箭。 布忽木看着它,又勾起他少年时候的思念。牧羊,放歌,在部落里面,比现在自由自在。布忽木拿过帖木儿身上的一张弓弩,拉来往天空射去,却只飞去五米高丈,完全没有力气。湛蓝的天空,有苍鹰盘旋的痕迹。 帖木儿笑着看着布忽木,布忽木从马背上胯下,吃力的捡起插在草地上的箭矢,无奈地笑了笑。帖木儿大声的狂笑,迅地拉开大弓,直把弓弩拉倒变形的边缘,箭矢流向空中,在苍鹰的脚下形成一道寥廓的弧线,却在一瞬间无力地坠落下去。帖木儿的眼神中带着错愕,他怔怔的看着布忽木,眼神不再放光,胸口赫然挺立地插着那支布忽木的铁头箭,布忽木在帖木儿弯弓射雕的一瞬间使劲了全身力气,帖木儿赫然倒下,从马背上重重的摔下,嘴里喘着热气,大口吐血。 “帖木儿安答,你忘记了我们的誓言。”布忽木半蹲在帖木儿的面前,把他的身体扶住,“如果我们失散了,请把那支箭安放在安答的天堂。”布忽木的脸颊上一道浑浊的清泪滑下,帖木儿挣扎着手抓住布忽木的衣襟,终于闭上了眼睛。 布忽木刺杀了帖木儿安答,他选择了离开了营帐,离开漠西,走得越远越好。
(六) 在遥远的大漠以西,还是一样。布忽木知道,一切都无法改变,他羡慕在天空盘旋的苍鹰,却又怜悯的看着已经逝去的土地。 布忽木靠在一处长着荒草的土丘边上,大口喘着气,喝着水,喉管里面却呛着血腥的气味。在土丘里面,安详地躺着瘦死的这匹老马,布忽木已经不知道这匹西域的马和自己度过了多少年月,也不知道是从哪个士官手中用不足五十锭的波斯铜币购买。他现在只是靠在土丘上,为自己死去的朋友做最后的祈祷。 天气阴色不定,冷风席卷着草地。此时在苍茫的大漠以西的一个地方,布忽木只想停下脚步。他从自己的衣带中看着一把无法闪着铜光的匕首,上面是“布忽木”三个字。布忽木大笑了起来。 “我的母亲,我的妹妹,细封都兰……”布忽木停止了笑声,目光对准大地和天上仅有的微光,他看见草地上的芳草开始出现了牛羊,马儿在快乐的奔跑,哈达戴在自己的安答的身上…… 布忽木的眼神开始变黑,慢慢的变黑,眼前的重影让他出现幻觉。他的喉咙上是一处裂开的血红色,他用自己的鹰头匕首刺向了自己的身体,也一同刺破了自己的心房和眷恋的家园。他抬头倒在草地,眼睛没有合上,仰望大漠西北的天空。 天空上是一片湛蓝色,什么都没有。 |

|
|||
| 【投稿】【 收藏】 【关闭】 | |||
|
|
|||
| 上一篇:癌症 | 下一篇:舍得 | ||
| 推荐美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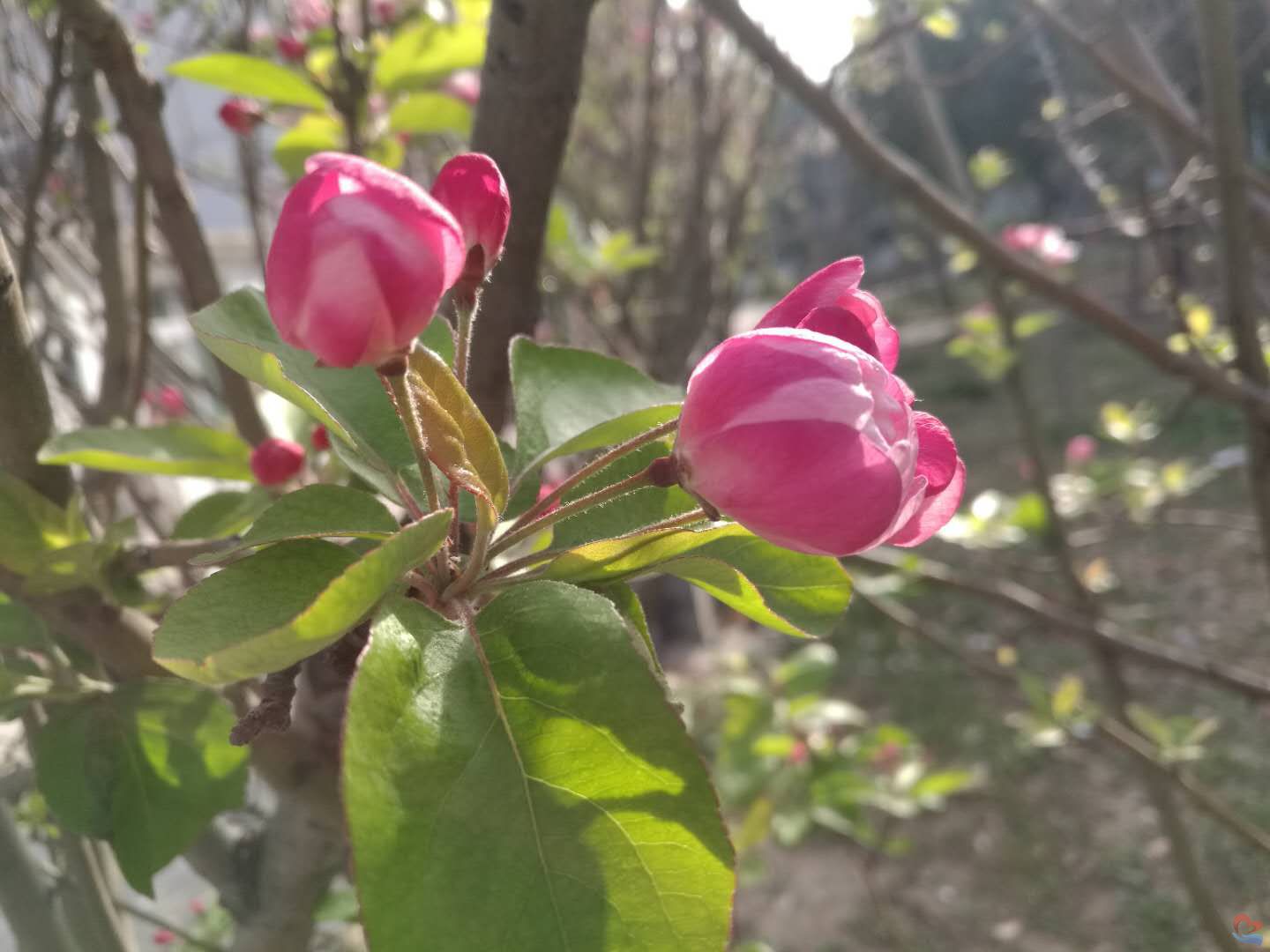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