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夕阳快要在地平线消失了,树枝上的小鸟凝视着,梦乡的到来。夜里我在夜莺的低吟中醒来。梦里还萦绕着母亲的身影。三千里外此刻正熟睡的母亲,在我梦里,真切的苍老了。
母亲体弱多病,可矮小虚弱的她竟经常去干那些与她身体不相称的农活。我清晰的看到了岁月硬是残忍的带走了她的容颜,偷走了她的健康,我也眼睁睁的听着母亲似有若无的病痛的呻吟。
母亲是个想得很多,可心里又老大想不开的农村妇女。她心很“窄”,多愁善感。儿子离家她难过,回来她也难过,只是难过的难过,开心的难过。她喜欢诉苦,喜欢倾诉。可以前却不喜欢听她唠叨,想想真是太不该。母亲是在苦难的家庭中成长的。从小放羊,吃不饱穿不暖。后来嫁了,又因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尚还年轻的她撑起了整个家。这二十几年也算是过来了,母亲讲着那些过去会泪流哽咽也会笑。
一个二十一二的少女,正是青春灿烂之际,却如此之早的就收起了那些本该属于少女的幻想,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我们身上。“那是我还是姑娘时候的事咯!”每当回忆起一点开心的事时她总这么说。可是,那短暂的二十年甚至是苦难的生活,纯真的少女会有多少幸福可言?
母亲不识字。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曾教过她一些简单的诸如“男”、“女”、“左”、“右”的字,可是她粗糙的双手始终握锄头比握笔更得心应手。除了她自己,没有人可以体会那不识字的痛苦。曾经她拿着药瓶问我们上面写了什么,可年幼的我们狠狠得回答了一个“不知道”。现在想想母亲失落的表情,尽是悔恨。有时她认识一两个简单的字就说给我们听,问是不是这样,上边是什么,下边又写了什么。现在的我总会耐心的去解释。她会像小孩子得到了糖一样满足,只因她也“识字”了。
从六年级起我就离家住校了。上了高中一年级两个月回一次家。现在更是半年回一次。每次见到母亲,第一反应都会是,母亲又矮了。是呢,时间把她身上所有的养分都尽数灌溉到了我们身上。
记得有一周忙了学习没给家里打电话,接到了母亲有些焦急的电话。开始一通责怪,然后嘘长问短。我放下笔,认真的听她说,我知道,她只是想听一声问候一个平安,她只想听听那声“妈”。
每次打电话问母亲身体的时候我都是矛盾难过的。就像我不敢问远方是否下雨,因为即使下了雨你没带伞我也无能为力一样。母亲总是说好点了,好多了。可是我知道,那苦痛的折磨我是知道的。放假回家时母亲正在住院,可等她稍好一些,我又踏上了去异乡求学的征程。身后的期望与泪水,我是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
秋天来了。文人笔下灿烂的喜庆的丰收,可是,那是母亲腰酸背痛强忍硬撑的季节。
我秋天的伤绪,不再是为叶儿黄了,夕阳落了,不再是天空黑了,梦儿碎了。而是,远方的母亲,又要受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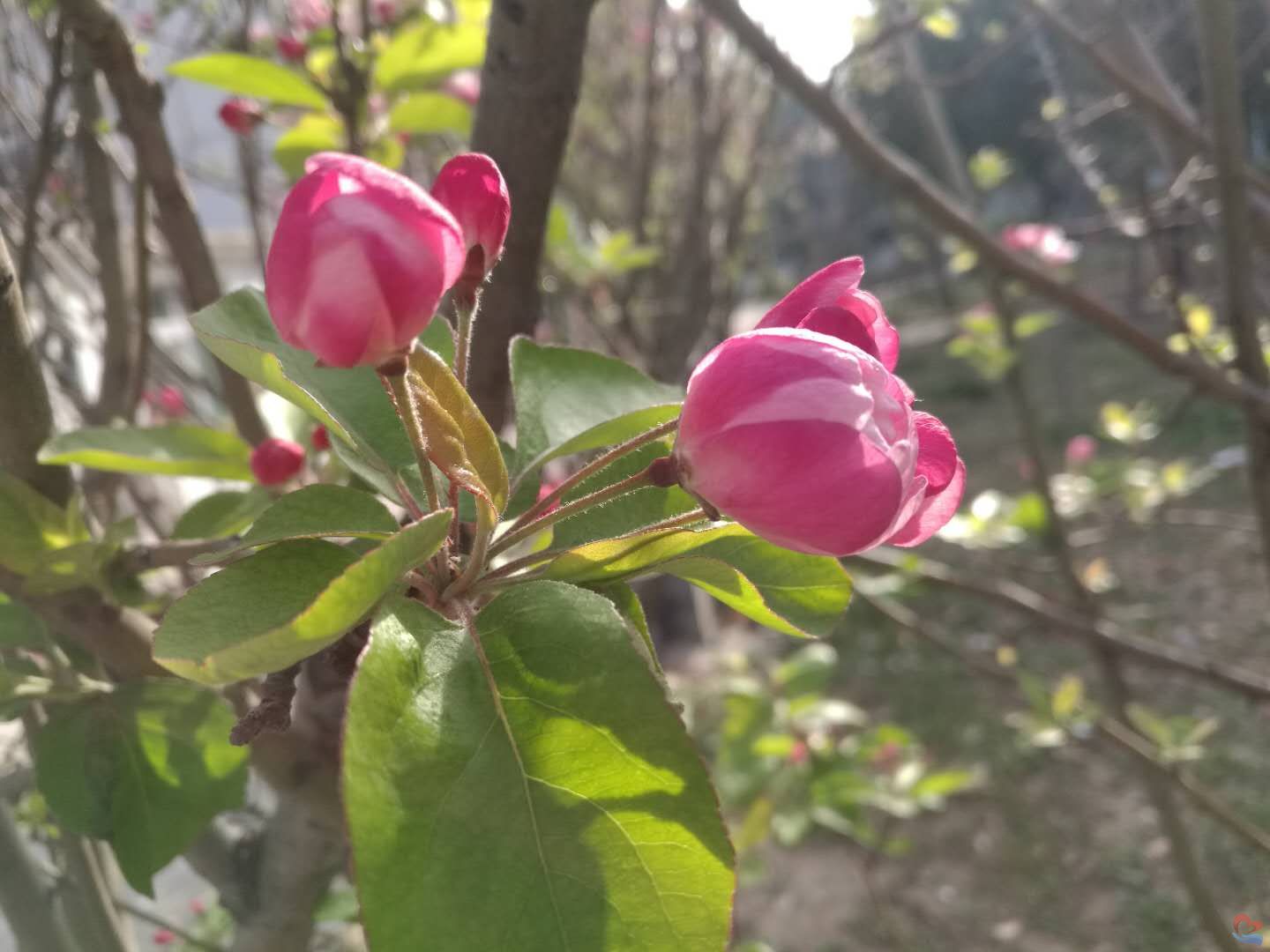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