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TOP | |||
|
江来纪事
管理
作者:甲申 发表时间:2015-03-11 18:03:32
评论:0条
关注
编者按:小说通过塑造清河村,宋氏祠堂的族人宋江来的人物形象,再现了清河村宋氏家族的厚重历史。也是中国民族厚重的历史演绎。朴实、厚重,历史变迁跨度时空长,人物塑造形象,历史底蕴丰厚,意蕴悠长,爱国爱家之情愫跃然纸上。文章旨意:不要忘记历史,不能忘记过去。荐读分享。 |
|||
|
三十年夜的两场寒雨,冰得彻骨,算起来下了两年。而清河村的人不一样,待到雨歇时,靠在青石屋外,空气冷得清新,印在在远处的山外,可以透出最美的时令来。年幼的润生被阿妈抱着,他的眼睛清澈的像天山的清水,仿佛是会说话一样。他比划着像未雕琢的细玉一般的双手,口中叫着阿妈的名字,又唱着旧时山外的童谣: “清河村,山外山,人到山里看青山;清河村,天外天,人到天上要成仙••••••” 润生是闰年的闰月所生,是我姐姐的孩子,按清河的族谱,他按堂族的“润”字排辈,而我自然是“水”字辈行。族谱上大抵是久远的过去,我想起时,只会暗自想得出“清,河•••江,水,润•••”的字辈,而润生却总能脱口而出,一一记住。我晓得他将来必有出息,便高兴地抱起他,他就干笑着,不说话。我说,润生好还是阿舅好,润生说阿舅好;阿舅好,还是清河村好,清河村好。清河村,如果擅长修辞,我不想概论他的美,只觉得是我的前世的山水,也是我现世的梦缘。我在清河村的地方长大,又因为工作回调到这个地方。新年的第一页,老黄历上写道:万事大吉。我把热菜夹到阿妈和阿爸的碗里,他们的皱纹又长了,笑起来把皱纹叠在一起,显得更加的多。阿姐抱住润生,听着新春的第一声爆竹。 火药味涂满了青石板上的泥路,听他们说,鞭炮放了好几个小时。我知道,在家里比什么都好,在清河的老家,比回到哪里都好。 清河村看起来很旧,四周的西南方向被山群围绕,说是山,按着这地貌上的路线走,大约只有丘陵的高度。山上种着茶树,在山下和山麓的屋子上,到处可以嗅到被泥土滋润和芳香萦绕的气味,我譬喻它是天山的茶花仙子,坐落在清河的山上。清河的水,沿着不规则的图案坐落在每家的灯火岸汀之边,青石上长满文字的青苔,河塘边沣草葳蕤。而我儿时的房子,像一个守旧的老人,在山下的河岸边聆听着这一方水土的历史故事。 我被调到临清河村的乡委,阿爸和阿妈为了庆祝我的乔迁之喜,特意为我倒上了绍县的老酒,我喝了一口就面部通红一直到耳朵根部。 “阿舅,你不会喝酒。”润生笑着,一直咯咯的笑个不停。 “谁说的,谁说阿舅不会喝酒,阿舅会喝。”我拿掉碗,当天居然拿起酒瓶就喝了。喝完就不省人事,润生不再笑了。 我很久才醒,方知不能喝酒,不然就倒进这无尽的水池里面了。 一九八四年的第一个新年的头一天,我居然在医院度过。阿爸把一包叠好的红贴递到我面前,说是江来叔寄来的。我迟疑的看着阿爸,不明白江来叔是何许人,只听得名很熟悉,算起来他的辈分和阿爸一样,是清河宋家的老长者,我定了定神,靠在医院的座椅上,想起了江来叔的年岁来,这才知道是他的九十大寿。 按理,我就应该去。在祠堂的周围,到处是宋家的族人,年长的老人宋江来的九十大寿,在四五米高的祠堂里面,我们拜谒了清河的先祖,又祭祀了清河的河伯山神,听到一声声爆竹的响声。清河的记忆又被拉得很长很长。 按照祖辈,我自然叫他叔,尽管他比我大五十多岁。宋江来跟我沾了一点亲戚的关系,是我父亲老堂的兄弟的堂兄,等于在这复杂关系的背后,是族叔这一身份未曾改变。我在祠堂里面行了跪拜稽首的三叩之礼,这年前,祠堂刚修复完整,我想,清河的往事又被江来叔誊录了平淡的一笔。 我也在江来叔的面前行礼,他颤颤的双手能看清楚很多的老茧。他在旁人的搀扶之下,把我扶起。江来叔已经老得说不出话来,我一直以为他太激动之故。他的头发已经花白的几尽掉光,被一个当地的剃头师傅剃着仅剩的头发,细矮的白色寸发一根一根的从身上掉落。这个剃头象征了新寿的九十期颐之礼,润生看着江来,小声的对我说:“阿舅,他哭了。” 可不是,过去江来叔就是行剃头的行当,从一绺的发丝到一寸一寸都是清河的历史。现在,别人帮他剃头,他想到自己吃过苦,想到自己的往事,谁不会落泪。 (一)剃头匠 按时间推算,九十年前,宋江来出生的地方还叫清河寨。江来的阿爸是当地的捕鱼人家,识得几个字,脱口一出:“清河江上来,莲藕画中卖••••••”也许那一天,宋江来并不清楚莲藕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只知道清河寨中,有山,有弄堂,有旧屋,有河塘。 一八九八年,江来叔只有五岁,可很多人都因为要剪辫子杀了头。 清河村当时有了新式的玩意,有了洋行买办,可没过多久,旧的还是旧的,学堂又变成了私塾。 江来叔的阿妈说江来总是不求上进,读不进书,只会做长工。长大了也是和自己一样的清苦人家。 但是,苦日子再苦,江来还是要去私塾念书的。阿爸说:“扬名声,显父母。”念书的唯一要求就是圣贤古训,或许哪一天,阿爸说江来在县城当官了,和洋人打了交道。然而,那些年以后,皇帝都被革命了,县太爷自然也没有了。 除了上私塾,江来回家还要帮阿妈砍下当天的柴火,生火需要力气,所以男丁人家自然需要多付出努力。清河寨里面多是短衣帮,穿着长衫的倒是让人尊敬,除了长者,年轻的学了新式的洋学就去了县城做老板,梳着油发出了宋家的族谱,不再回来。 江来叔也去过县城,那是穿着短衣的串街的事情了。 翻过新历以后,康党变法革新的旧学变成了惑众的妖言,清河寨听说也有进步人士,是那些戴了假辫子的洋学党。那天江来看见过,那个人被乡邻在私塾门口一揪,假发就掉了下来,露出了整个秃瓢,大伙儿都乐了,半个秃瓢的真辫子取笑了假辫子,结果把私塾老师一激,狠狠地拍了教尺,声音就消退了。 “顽劣无知,不成器也。此五十步笑百步尔。”老先生穿着旧学时的窄肩马褂,头发已经花白,却还字字铿锵有力。他把镜框别在鼻梁的下沿,又拍了一下教尺。 “先生,你刚才也笑了。”不知为什么,宋江来说了这一句,别人的目光就盯着他了,老先生也盯着他看。 老先生让宋江来站起来,示意他背文。“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宋江来马上就把《礼记》里面熟知的一句说了出来,谁知变成老先生一句暴戾的大骂。 “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老先生摇头说完,把教尺一放,宋江来根本没有听到老先生的讲课,只顾自己的思想漂移了清河寨的窗外,窗外的晴空很美,不像在屋子里面迂腐而压抑。 老先生示意宋江来做一番解义,在解答过后,教尺三声打在宋江来的手心。“不知学,所以犯困。”这是宋江来的回答,结果老先生告诉了阿妈,阿妈揪起了宋江来的耳朵,直到晚上宋江来也睡不舒服。 按理,谁都有学习的天分,可老先生偏说江来小儿无知不可教,阿妈也气了,只能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雨过以后是清河寨上最好的阳光照在茶树上,山坳上面还是孩子的笑声。这一年,江来八岁,阿妈又为江来增添了一个弟弟,阿爸说,他叫“江生”。 江来抱着弟弟江生,阿妈的脸色却一直很凝重,她知道日子清苦不能维持生计,阿妈背着背篓采完茶叶,从江来手中抱过江生,江生一直哭,都快把嗓子哭哑了。 “江来,你不能再念书了。”阿妈哄着江生对着江来说。 “为什么,阿妈。”宋江来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只知道他又多了一个生活的玩伴,而阿妈却觉得生活中多了一副粗瓷碗筷。 “生活清贫,你需要跟你三叔学艺谋生去了。”阿妈平静的说着,脸色的气色却一直很差。 三叔是江来的远房堂叔,他在离清河寨几里的县城商铺,他做着剃头的行当,当时的辫子是半剃半留,剃头也颇为讲究。师傅带着徒弟,一个背着箱子,一个拿着旗杆,像是行医的行当,但县里人只是说:“伊是串接卖艺的。” “串街卖艺的来了——”县里的小孩嘴里含着糖葫芦,大笑着跟着瞎起哄。 宋江来含着眼泪辞别了父母,他知道自己不是有违圣贤的话。“扬名声,显父母。”谁都知道剃头匠并没有什么前途,只是贫寒中讨点生活罢了。 宋江来跪在地上,双手举起清茶,做了稽首之礼,算是给三叔拜师学艺了。 县城的街边开设了机器厂,邻水的码头边非常热闹,都是卖着苦力的长工。至于穿着长衫的,要不就是低下的说书先生,另一部分却是腰里先发富的盐商。 这一带有人买盐,有人开药坊,都成了有门面的老爷和老板。嘴里有新鲜的英国维多利亚的公爵烤瓷牙,脖子边上有法国人的玛瑙石,他们的辫子还没有剪去,沿着乌黑的发丝顺着清河的江水,真是漂亮极了。 宋江来好容易找到三叔,三叔的家里门板被弃放在一旁,他和短衣帮的长工租住在一起,里面燥热和汗臭不时的传来,听说他们要去河流里面洗三次澡,江河水很浑浊,他们说里面有康党的死人,经这么一说,很多人不去江里洗澡了。 光绪年已经实行剪辫子,可三叔是个老实人,他喏着身子,驼着腰背,在上等人面前他说不起话,所以他没给老爷官家们剃过头发,下等人只管老老实实干活,三叔刚给一个长工洗完脸,把辫子重新盘在头上两圈,就算完事。收了几个铜板,算是解决一点家用。 三叔几年来也没给江来教过一些本事,只是让他串街时拿着旗,吆喝的声音大点,就管一顿饱饭。 “师父,为什么跟您三年,你都没教我这份工?”江来赤膊着,大夏天非常热,他吃完饭怯生生的对着三叔说,对于这个很多年一直没见的三叔,他一直叫他“师父”。 三叔迟疑了一下,没有作声,把碗撂在一边,眼睛看着宋江来没有放开。“剃头之行,没有出路,不能显贵,所以你从我门下,什么都是从首而起。” “首,对着剃刀。可不就是一直从首而起,所以做人也一样,脚踏实地。”对于三叔的这句话,江来一直记在心里。很多年以后,在祠堂祭拜的时候,我看着江来叔提到三叔的名字,他还会动之以情,流下眼泪。 几天以后,江来也有了一个普通的箱子,箱子里面有小抽屉,拉开长方形的小小的抽屉,上面都是灰尘,这是三叔很久没用过的那一份箱子,这下给了江来,里面有火罐,剃刀,剪子,还有一把破旧无比的梳子,梳子上面还有几根头发黏在一起。 江来把这些东西清洗一遍以后,算是和师父共同串接闯江湖了。“剃发髠落,从首而始。” 头几天,求江来剃头的,一个都没有,还是三叔赚到了几分银两。 “江来,剃发髠落,从首而开。”这是三叔教给江来的第二句话,江来牢牢的记在心里,喝完茶,他就背着箱子,帮着几个商客捡起了头发。 没几天,江来和商人起了口角,他们居然奸诈的连几个铜板都不给,对于十四岁的江来,他第一次收到心里的不痛快。 夜里,三叔把门板栓好,点上煤油,在桌子上用手蘸着水写下几个字——求得万事兴,方从刑首立。这是三叔交给江来的第三句话,在县城里面,江来开始用眼色查人,给哪些人剃头,给哪些人不剃头,他都心中有个数。 “官家行头,为你盘好。”江来帮着给长工刮脸的工夫,和长工叙旧。 “你是清河寨人?” “是啊!” “出来做工?” “是的,养活自己。” 江来把长工的散开的辫子梳理干净,又仔仔细细的盘好在头顶,“官家,您走好。”江来又背起箱子向前走去。 江来赚到几个银两,在县城的烧鸭铺面前买了一只烧鸭,算是给三叔买的。三叔看了很高兴,说江来居然长得这么高了,不像从清河寨里面刚出来的样子了。 江来离开清河寨已经很多年了,他回去过几回,已经抱不动江生了。江生怕生,说着假话讨厌江来,其实他觉得江来很好,因为江来一直给弟弟寄去烧鸭,只要一吃县城里的烧鸭,江生就说哥哥好。毕竟那是清河寨里面吃不到的,阿妈说,江来有出息了,江来知道,那不是真的。 傍晚,码头上的夕阳照在江上,是一片壮丽的诗画篇章。然而辛苦的本钱还在继续,江来急急忙忙的背着箱子从青石街上赶到家里,他找不到三叔。 原来三叔就在里屋,他一天都没有出门。江来给三叔熬了米粥,让三叔喝下,三叔的胡子茬非常脏乱,江来隐约的赶到三叔变得瘦小了,也是因为自己变得高壮了,江来已经像码头的长工一样有有力气,而三叔的力气却变小了。 “江来,你且喝下这碗茶。”三叔难受的说道。 江来迟疑的看着三叔,才慢慢的喝下清茶。 “江来,你我师徒情份已尽,你我不再是师徒,你自己谋生去吧。”三叔平静的说,却很有力量。 “不,为什么,三叔,师父。”江来不敢相信,“如果您觉得您的徒弟没有出息,你可以骂我,甚至打我,总之您不要赶我走,说这样的决绝之话呀••••••” “不,你长大了。你刚才喝得茶,是谢师之礼,你要自己去讨生活。我不能管你的饭了•••师父老了。” “不,师父。”江来哭了,但觉得三叔说得有理,他牢牢记得三叔交给他的话,一直记在心头。 江来临行前,给三叔行了稽首之礼,离开了三叔。 “串接卖艺的来了。”小孩子还会年轻,他们说着以前小孩说的话,江来已经十八岁,他没有回清河寨,在县城独自背着箱子,拿着旗杆,像一个游行僧一样讨生活。 “剃发髠落,从首而始。”一九一二年,时间有翻走了一页,清河寨的天边有枪声想起。 (二)出师 江来和东边的日出赶着时间,为了谋生,他选择起早赶集。他走了一圈,在凛冽的寒风中来来回回,热闹的街道上变得冷清了许多。 县城有个田家老宅,是县绅田老爷家的府邸。上面可见的灯笼已经暗了许多,承蒙上流人的关照,江来进了府邸做工,工钱自然也是长了。 江来为了给田家小少爷的儿子做满月,田家人可没少花心思。他们从市集上找了十个串街的剃头匠,为的是甄选最合适的人选。田老爷说了,剃头匠要找来年轻的,不然小少爷看见他才能长成英俊的后生;剃头匠得认得字,小少爷看见他才能提笔写文。可选来选去,一个个哈着腰的剃头匠被像长工一样似的赶了出来。江来十八岁,有些英气,身材高大,少时读过点私塾,自然认得字。 田府的管家看着他的样子,身形高壮的小伙,一条长辫子倒在正中的背间,眉宇间炯炯有神,可一发出声音,却是怯生生的。 “田老爷好。”江来说话有气无力。 “我是田家的管事,一会传呼你进去,你才可叫‘田老爷’”。管家特意吩咐了江来。江来出行很多年,遇着很多人自然也叫着“老爷”,叫的多了,自然也熟识了。 江来走进府邸,四周是环笼的大杂院,有各异而不同的高矮的房子拼接在一起,江来总是认错路。这里规矩很多,按古训之说,要立功立德,他总要和管家一起端手作揖在门前,管家才会在屋外喊去另一个管事,是传令的意思。江来总是见一面田老爷要一炷香的钟头。时间久了,身子就会和管家一样,弓着背,欠身地低头看着老爷等待发话。 江来和管家一动不动,站在院门之右,向田老爷的左房门前作揖三次,才能等到传话,开门的是房门丫鬟,等到丫鬟往田老爷房门的管家处传话,江来再从田老爷房门作揖三次,田老爷方才有伸着懒腰在阳光下慵懒的动静。 田老爷披着一件黑色的马褂出来,衣装颇有讲究,上面纹饰旖旎,绣着端庄金凤,是大富人家令于当地名人绣工坊张老板所做。田老爷戴上新鲜的西洋镜,对着日光满口诗文熏陶: 暖日迟迟花袅袅。人将红粉争花好,华不能言惟解笑,金壶到,花开未老人年少•••••• “老爷,宋先生已在院中等候多时。”管家对着田老爷小声的说道。管家的脸有些饱满,他带着黑色的瓜皮帽,田老爷也戴着瓜皮帽,只是田老爷的中间是翡翠的帽正,而管家的就没有。 “让他等着吧。”田老爷随口的说,只是抱着他的小孙子田小少爷一直乐在其中,没有理会其他人。 田老爷的院门墙角是随处可见的礼聘,是十几个长工抬来的,院门外有个红漆的轿子。田老爷这才出门迎接。 轿子里面出来的正是清河张县令,他带来了对田家小少爷的千纸银票,还有湖州产的毛笔,是寄予田家的文风永久之意。田老爷笑着和张县令谈话,江来又在院门苦站了很长时间。 院子里面有很多事情吩咐,主房宴宾,张县令是上等的客人,除了攀谈国事一点,大多是讲着家事。下人们早就被吩咐了出去,江来没有见到田老爷,就被管家带到乐工身旁。 为田家小少爷行满月礼自然离不开乐工,他们大多也身份低下,比他们更低的只有戏子和乞丐。江来和他们坐在一起,却聊得很开。 “你是清河寨人否?” “君也是?” “伊都是。” 乐工乔满吹着民乐胡琴,向江来弹奏了一曲。江来仿佛听见了清河寨里面山水的花月之夜,有家乡的歌者在清灵的河水上翩跹。 满月酒,是江来行剃头行当以来规矩最多的一次。按理他穿着长工的红色短衣,却被归置了一身长衫,是为显小少爷的身贵。 小少爷一直哭,江来剪不好头发,还被他抓了一把。那天,江来根本没有赚到一分钱,田老爷把他像丧家犬一样赶出了院子,说,不要再出现在清河县城。 江来终于没有回田宅,因为闹了革命,宣统年不见了,皇帝变成了大总统。找江来的人突然多了起来,不为别的,就是为剃刀缠绕身上已久的辫子。 江来的辫子是自己剪的,他仔细的端好自己的头发,像珍藏自己的子女一样看着,《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今,革了命,也革了头发。 年关将至,大伙看看对方,都笑话了自己,像个半秃瓢没长好头发的乞丐。头发有时也象征了新的希望,江来写信送到清河寨,他对阿妈说,江来很好,对江生说,哥哥很好,换了个新的时髦头发。 这几年,学做剃头生意的串街人自然多了起来。摩登的女郎要求新时髦的手艺,阔太要求最时装的巴黎秀,还有那些从宁波或者去上海的富商,穿着西装换了三七的伯爵头型。 剃发髠落,从首而开。三叔的话变成守旧的代名词,却还是让江来回味很久。他知道,他学了新时髦的剃发的手艺,革命党任然在革命,做老爷的还是穿着旧行头浮夸的和官绅打交道,而自己还是和做长工的一样,一样匍匐着做人,或许清河寨会好很多。其实,也都一样。 江来回了清河寨,阿妈给江来找了个姑娘蓝月,蓝月是清河寨的外姓人家,名字秀外慧中,却是大字不识。乡下要的是姑娘的勤快,至于其他,就是生孩子为重。 江来带着蓝月又回到县城东奔西跑,一晃几年,县城铺上了马路和电缆,有电车开过,里面谁都可以坐,人人平等。那时,每次回清河寨,江来必然炫耀一番,让江生好生羡慕。 “江来哥,县城有好玩的地方,可以带我去吗?”江生已有十二,却还是像孩子一样顽劣。江生天性比江来好动,旧私塾改成了新学堂,江生也不愿意学,倒也听得了新鲜名词。 “江生,哥哥只是去县城串街。” “串街,卖艺吗?” “不是,是给人剃头。哥哥是匠人。” “匠人?是和宁波的老板一样吗?” 江来不知道新学堂里面有什么新的词汇,总之江生时不时的蹦出这些名词的时候,倒让江来变得局促起来。江来知道,他必是老实人,而江生不再要守旧,不再局限在清河寨,他会“显父母,扬名声。” 蓝月生了,是个大胖小子。按清河的族辈,取名水炆,有水火之意。可字义虽好,日子也变得拮据,常常入不敷出,只得不停的来回折腾。 一九一七年,张勋这个肥头大耳的人搞复辟,辫子几天之后又流行了起来。可时兴的辫发对于江来来说,是个很好的营生。赚了些银子,却被挤在枪炮口。 “你是辫子党吗?” 由于为辫子党修过头发,江来被革命党人的枪口指着,手中的剃刀垂落在地上,手一直不停的发抖,没有说话。 因为头上没有辫子,江来终于夺过了一劫。他知道县城不能再待,只好带着蓝月和水炆往县城的码头赶去,他要回清河寨。 (三)战争 在清河寨的日子也没有好过,江来娶了媳妇自然是新添置了房子搬出去住。而江生整天神神叨叨,学了几天新学就说要走出清河寨,冲破屋里的藩篱走向新世界。阿爸没少生气,终于被气病了。 阿爸好久没有外出捕鱼,家里唯一的支柱倒下,江来自然要承受许多。尽管蓝月不忍,也只好把用红纸包好的一叠银两递到阿妈的面前。 “阿妈,这些钱您老拿去用吧。” “使不得,使不得。你也生活不易,还有水炆待哺。”阿妈一脸亏欠地说。 “不,阿妈对我养育之恩,小钱小恩当为江来所报德之时啊。”江来一再的推阻,才让阿妈收下了银两,可江来行剃头行又能赚多少钱呢,只好多用心血来求门路。 清河寨当地的老爷是江来的本家,叫宋海元。是宋家宗祠上一辈的家长,早年通过买卖茶叶发了财,得到一份地产。他每天除了叼着烟嘴打发时间以外,就是和一些宁波的当地盐商,茶商交谈生意。 江来除了剃头人的手艺以外,就没别的本事,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但好歹能卖力气。和当地的长工王德山一商量,决定去求宋老爷的家里。 宋老爷刚翻修了自己的新宅院,又添置了两房姨太,相比于江来的拮据生活,宋老爷的日子是滋润的可以。他倒也做了不少让清河寨称道的事情,年前他把清河寨的宗祠的破损的墙角重新翻修了一遍,虔诚的拜了稽首,双手合十,念德道仁,好让祖先保佑自己的一方平安。 江来和王德山点着头,蹑手蹑脚的在宋老爷的家里无聊的徘徊,终于等到宋老爷的到来,宋老爷一身的丝绸长衫,手上带着一颗绿色的璞玉环,脸上笑嘻嘻的看着江来和王德山,没有说话。 “宋老爷,我们有事相求。” “有什么事呢?”宋老爷悠闲地躺在太师椅上,心知肚明却没有说出来。他只顾着喝茶,这茶叶是自己进口的洋货,他知道自己的茶叶苦,卖了别人家,自己当然不喝。 “我们想向您租田。”江来怯生生的说。 “租几亩。”宋老爷没有抬头看他们,只顾摸着手指上的璞玉。 “我想租五亩。”王德山率先说道,王德山是个率性的瘦子,干活麻利没有怨言,除了别人骂他,他才会骂娘。 “你姓什么?” “我姓王。” “这样吧,你先签一下字据。我把三亩荒田租给你,你需从字据上的条例按时交税,从你工钱上扣。”宋老爷收起笑脸,一脸严肃的说。 “那是,那是。”王德山知道自己签了字据以后,连声的维诺。 “你叫什么?” “宋江来。”江来平淡的说。 “哦,既是本家。我就把三亩好田租给你,你且记得。”江来连声感谢,知道自己可以卖点力气活来养活家人,蓝月在家戴着两岁多的水炆,喝着稀粥,人也瘦了不少,但签了字据总归好点。“你会点什么。” “我会剃头。” “哦!”宋老爷咯咯的笑了,“那你说说,时下米行的张掌柜的头型怎么样?” “实不相瞒,张掌柜的头发是我剃的,不才剃得一般。” “年轻人,不错。”宋老爷抬手叼着烟嘴,余烟在一米高的空气中袅袅腾空,像婀娜的舞女在跳舞一样,“很好,我以后有事剃发就找你了。” “谢谢老爷。” 王德山却不痛快,一样的佃户,因为姓王而吃了亏。这个瘦子表面没说什么,背后就骂了起来,祖宗八代都骂上了,他知道自己反正不是宋家祠堂的人,顾着自己就好了。 江来回到家,两手并作四手用,蓝月害喜,又怀上了。江来高兴之余又害怕了,因为日子本来就不富裕。 宋老板还是一样,表面嘻嘻哈哈,却总是喜欢在弓着背的长工和佃户面前颐指气使,风光不已。他又在和一些当事的掌柜们探讨茶叶的价格的时候,可以舒展一些自己的心情。 夜晚的清河寨,晴空诗意。江来却一直睡不着,水炆好容易睡下,江来不时的辗转反侧。这几天,江生说要报考军校,可学费不仅用。罢了,罢了。江来自己都管不住自己。 阿爸一直卧病在床,不时的呕吐,听说是患了胃病,可吃了药记的草药还是不见好。几年以后,阿爸走了,江来的喉咙几天都是沙哑的,嘴唇干裂的说不出话。清河寨一脸下起了好久的雨,临近杭州与宁波的铁路被泥块堵塞,江生背着背带,含着泪,去了外省的县城读书去了。 江来抱着已经长得很高的江生,也哭了。把包好的红色的纸袋塞给江生,这是江来几天没有停歇的做佃户的工钱,淋了几天雨,嗓子坏了,用哭代替了话语。 红色的纸袋里面是包好的银元,江生也哭了,知道自己哥哥为自己的生活负担了脊背,江来的背一直挺不直,被汗水和热辣的阳光压弯。 江生离开了清河寨,蓝月却给江来又生了一个男娃。水炆比水仁大三岁,水仁被蓝月抱在怀里,蓝月的干瘪的乳汁抚慰不了水仁的营养,而水炆也小,生活更加不济。阿妈在阿爸离去的很多天里面,一直在祠堂里面守着,按理江来要去守孝,可现在的时节不讲究,人要饿死,只能退一步生存。 爆竹声在祠堂上面响起,叩首在高堂,还礼在旧乡。宋家祠堂迎来了江生的婚礼祭祀,江生拜了祖先,也拜了阿妈,还拜了江来阿哥和蓝月嫂子。水炆和水仁长高了一些,却没有江生阿叔高,而江来的身子却变瘦变矮了。江生有出息了,江生扬了名声,显了父母,江生娶了县城女校的张掌柜的千金,算是有了新的福音。 下午,滴水在屋檐穿过,是清悦的声响。江来拿着剃刀,正为宋老爷的仔细地修面,剃刀清晰的拂过他干燥的脸,像一道平静的流水波澜不惊。宋老爷也渐渐的老了,他正闭着目,享受着下午的雨后阳光。 “江来,你的手艺又长了。”宋老爷笑着说,对着镜子里的头发高兴的说。 “那里,都是承老爷的福。”江来只知道尽下人的本分,领着额外的工钱是新添置的收获。可日子却不知不觉的走过了,转眼间江来也过四十了。而水炆也长成了二十岁的年纪,成了英俊时髦的小青年。 不知为什么,祠堂的泥墙突然有一天倒塌了,宋家人拜了凶礼也不经事。天边又想起枪炮声,是空气中嗜血的味道。 听江来叔说,日本人进寨的时候,他刚去了县城。日本人抢了女人,也杀了人,宋老爷的儿子也被日本人打死了。 外运的茶叶商被日本人截下,宋老爷人很刻薄,却誓死不答应要日本人承接生意,宋老爷理智的说:“宋家的祠堂看着,我再无能也不能把祖先的地方给了杀人的畜生。” 日本兵很快就占领了清河寨,他们想屠村,又觉得这里闭塞落后,只留了小分队在这里驻扎,只是杀了几个人了事。 江来在县城里面也回不了清河寨,他知道日本兵的可憎,却见不到阿妈和蓝月无论如何都要回去。 他刚坐了轮船,就碰到满嘴胡语听不懂话的日本宪兵队。他被抓到一边搜了身,日本人没有查到他什么,只好放了江来。 江来叔说,要不是江生提前预知了路线的转移,江来叔一家人都会被杀。听到这里,我安慰了江来叔,江来叔九十岁生日一过,人也没有精神,我试图唱起了歌安慰他,哄他开心,他也只顾着乐了。 润生只顾着问我,他当然没有经历过去,也不知道我江来叔和江生叔的一些事情。江生叔当时是新四军的民兵连长,也是他打跑了鬼子,还了清河寨的一片安宁。 江生读过书,早年就投了革命,听说杀鬼子,他第一个上了枪膛,誓死在这一片土地上血拼。 这一天,天空居然一片阴翳,却没有下雨。村民们变得很少,只有血污的河塘和干枯的树丫,旧屋廊和茅屋大抵被破坏了,田地上很久没有长上稻子,到处都有被踩踏的痕迹,变成一块荒地。 “连长。”水炆也当了兵,对阿叔江生这样喊道,他们在清河的山坳边挖了埋伏,地雷声火光四起,鬼子的军帽掉了一地。 “水炆,我们进攻。杀!”子弹穿膛而过,新四军的民兵连在清河寨的风雨之夜留下了撼动山神的事迹。 水炆倒在血泊中,身子上到处是血,江来抱着他,久久没有回过神,江生也哭着,蓝月和水仁的哀嚎在清河寨的今天也能听到。 宋家的祠堂经过了好几次翻修,这是宋家人的心血。打完鬼子,这里是一地的废墟,山神没有保佑,宋家的人捍卫了祖宗的沃土。 这几年,江来和蓝月只有水仁一个孩子,独自把他拉扯大。而水仁按照祖辈,既是我堂兄的大哥。 (四)大队长 清河寨的祠堂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修理,直到土改以后,清河寨变成了清河大队,有过一次修整。 土地没收以后,一些老爷姨太官家没有了活路,宋老爷年岁已高,已经走不动路,却还是被一行民兵队押着,连带一起的还有县城的田老爷和张掌柜。田老爷这个人,江来当初在县城见过,已经没有当初的神气。他也有七十多岁,据说他的几房姨太太都和他闹了官司离了婚,田老爷成了孤家寡人一个,而一些少爷们自然也没有了,想看也不去见他。 江来突然都一个人很熟识,原来是王德山,那个曾经和自己一起向宋老爷家讨租地的佃户,如今成了王德山副队长。王德山抗过日,杀过鬼子,复员以后分到地产,大伙一起吃食堂饭。 “德山同志。”江来给王德山敬了个礼。 “江来同志,都好吧。”王德山回敬了一个军礼。 “都好,你呢?” “哦,我真审着他们呢。”王德山和这些乡绅们讨要土地,官家老爷的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他们也老了,却什么都不会做。 江来不再是佃户,江来有了自己的土地。清河的土地,大伙种;清河的稻子,大伙吃。这是老一辈人说的话,我小时候听阿爸说过,也听江来叔说过。 那些年,祠堂边上是食堂公社,大伙吃食堂饭的日子对于江来这个剃头匠来说是最得意的一天。江来的皮肤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变得黝黑而干燥,而蓝月也变成了年过半百的女人,水仁这一年结了婚,娶的是当地的大队宋家女。 公社成立的时候,江来托大家的福,亮了自己的老营生,给大伙儿剃了个头。“剃发髠落,从首而始。”据传剃头匠是髠刑官而生,掌握了别人脑袋的生杀大权。 “江来,你给我剪个好看的发型。” “行,就交给我吧,谁叫我是大队长呢?”江来开起了玩笑。 “江来,下次大队选队长的时候,我就投你了。”大伙也开起了江来的玩笑。 从这以后,不管是谁,都管江来叫大队长。既然是大队长,大伙有忙的时候,江来自然要帮,可江来无奈的说:“老了,帮不动了。” 江来发现自己的头发已经有了白鬓,儿子水仁也有了儿子,江生把小孙子阿润抱在手里,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而江来面对的最不幸的是,让阿妈的死在这一天成了遗憾。 阿妈走了,带着清河寨的遗憾走了。阿妈没有享过几天福,江来知道,无论自己穷尽毕生,也报答不完阿妈的恩德。 江生后来去了县里工作,江来一直就没有去县城,他说,我是清河的大队长,不去县城了。江来知道,县城的三叔早就不在了,夜里的下雨天,江来老泪横流,一夜未眠。 从那以后,雨夜没完没了。谁都没有办法,因为这样,余粮只能吃几天,稻子长不好。稻子像蔫黄的样子,烂在泥壤当中,储水的地方是低洼的池塘,水都淹死了粮食。 “大队长,大队长。”江来家的屋门响了,和天上的雷声一样。 “大伙没有粮食,吃什么呀。” 在宋家祠堂边,大伙聚在一起,焦虑的对着祖先的土地,没有一点办法。 “不要急,我去想办法。”江来毫不犹豫的说,大伙说,天无绝人之路,多亏了江来“大队长”。 江来一连去了几天,联系了县里的江生,好歹把余粮征调下来。公社食堂把米饭专门熬成了米粥,像浓稠的情感流淌在夕阳的天边。 江来雨天去了县城,得了感冒。只能在家里围着火,烤着衣服。 “你看,非说自己是大队长。逞能以后自己吃苦果。”妻子蓝月一边给江来熬粥,一边抱怨起江来。 “没事,淋点雨没什么。大伙都有饭吃了,我们以前饿肚子,我们的孙子不会饿肚子了。” “这怎么说。” “因为我是大队长啊。”江来看着孙子阿润的修玉的嫩手,傻傻的笑着。他知道自己不算什么大队长,但大伙有困难,就要帮助大家。 蓝月也笑了,他说江来变得油嘴滑舌了。 江来大队长最后还是没有行使“大队长”的职责,他还是干起了老本行——剃头匠。 江来叔从一个少年剃头匠变成老剃头匠,不管在县城也好,在清河寨也罢,都守着自己的本分。 “串接卖艺的来了。” “不,是剃头匠来了。”江来不需要像过去那样拿着旗杆,只是背着小巷子,在风声中大声的笑着。 在清河大队的时候,大伙叫“大队长”来剃头,江来也是有求必应,是分文不收。江来说:“求得万事兴,方从刑首立。” “这是谁说的。”孙子阿润看着老江来,傻傻的天真的说道。 “是我师父说的。”江来打趣地说。 “师父是谁?” “师父是三叔。” “那三叔又是谁呢。” •••••• (五)江来的今生 我抱着外甥润生,听完了江来叔的故事。老家的祠堂在我工作以前,又大修一次,那次被红卫兵打翻了墙头,要破四旧,连祖宗的宗祠也要砸。 清河村的宋家祠堂终于修缮完整,我想到这里,又看着江来叔,他像一个历史老人,驻守着这片清河热土。 八几年的时候我还在清河村,清河村变新了,通了铁路和山路;清河村变旧了,还是旧的茶树和茶香。曾经,总想羡慕未来的日子会怎样,却仿佛有一种想回到过去的冲动。我和润生一起,慢慢的走着山路,他痴痴的数着茶花,一朵一朵,怎么也数不完。 “润生。”我叫了润生一下,我看着他,笑了。 “咯咯咯••••••”这个孩子笑得真开心。 几米高的祠堂上又点燃了爆竹,声声回畔在我忆乡的思绪里面。我点好香烛,等待着老人们在祭司的念词中行礼。 “一叩首,拜。”祭司戴着传统的汉冠,穿着传统的衣裳,主持着祭祀仪式。 我行了稽首礼,看着面前的清河宋家祠堂。 “二叩首,拜。” 我和江来叔行了稽首礼,清河祠堂在祖先的身体血液里面流淌。 “三叩首,拜。” 我和江来叔,润生行了稽首礼,清河祠堂,在今生,在今世•••••• |

|
|||
| 【投稿】【 收藏】 【关闭】 | |||
|
|
|||
| 上一篇:去留 | 下一篇:对不起,背叛你情非得已 | ||
| 推荐美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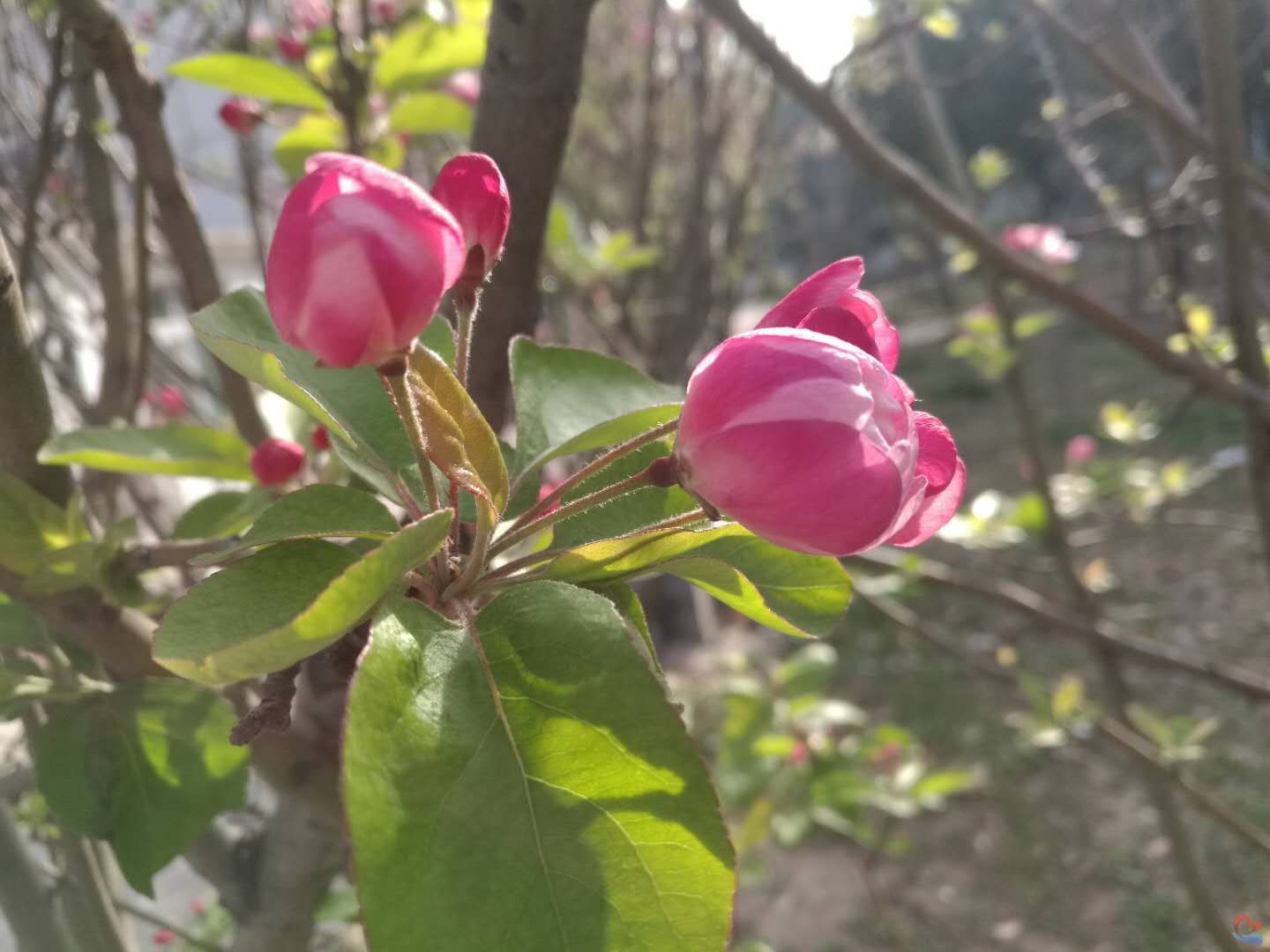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