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大军二军小哥俩,一人开一辆轿车,把我们哥儿四个从烟台一溜烟地载向威海。
刚进威海,内心就生出了些许疑问:这高速怎么修到山上了呢?这数不清的大坡子,一个连着一个,才刚下了这个坡,还未来得及歇气儿,立马又朝那个坡发起了冲锋。个别的坡,陡得甚是吓人,车子箭一般地射下去,外面肆虐呼啸的风,似乎要把车窗撕裂一般。我惊恐地闭上眼,生怕前方万一出现什么状况,感觉这车定是刹不住,人无论如何是无法驾驭它的疯狂的。耳畔呼呼的风声渐渐小了,感觉车子的节奏慢了下来。我忐忑地睁开眼,张望着,车正驶上高坡。
嗬——鳞次栉比的高楼,似乎就在脚下;远处有浩瀚无垠的海,海上有大小不同的船;高低不平环绕着大海的山;山上有一片片葱郁的绿树,还有一层一层的梯田。大风车亭亭玉立,不规则地分布在山边或是路边,随着车的前进,不停地向我们迎来,又被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
早听人说威海是个好去处,这次竟不经意间就来了,在这,是否有我们这些平凡人的一席立足之地?我不敢再去臆想。
“姐夫。”大军喊了我一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我微晃了一下头,见他嘴一呶:“看见没?楼门口站着的那个秃子就是宝子——你们的老板。”
顺着大军的目光往前瞅:果见一胖乎乎的秃子站在一栋有些斑驳的楼门前,手搭凉棚,往这边张望着。我心里想:怎么有点像地痞恶煞?!
车还没停稳,老板就迎过来:“呵呵,大军,终于把你盼来了!”他俩又是握手,又是拥抱,那个激动劲让人羡慕。大军向我招招手,拉着老板说:“这是姐夫。勤劳、能吃苦,啥说的没有,好活挣钱多的,你就多照顾照顾姐夫吧!”老板握着我的手,姐夫姐夫地喊,又递烟又问我什么时候从家出来的,那个亲热劲,好像比对自家姐夫还亲。我的头有点大,从没见过有对我如此热情的人。尽管知道人家是看大军的面子装出来的,反正心里很是受用。我有些尴尬地点头示意,语无伦次地喊了几个兄弟。抬眼看他:圆脸,胖嘟嘟的肉把眼睛挤得好像睁不开,但我仍能感觉到他眼里有几分让人不寒而栗的煞气。油嘴滑舌的腔调,会屈会伸的样子,很像电视剧里地主家的阔少。
“想死我了,宝子!”这时,二军刚从车里出来,就夸张地喊。宝子迎过去:“我也想你啊,军军。”宝子故意奴奴着小嘴,娇滴滴地喊,停顿了一下:“可是,想你想得都想不起来了。”俩人哈哈地大笑,我们都跟着笑。大军说了句:“四十多岁了,还那玩意。”二军搂着宝子的肩,宝子象征性地当胸一拳。二军说:“姐夫就交给你了。还有那几个哥哥,都是咱家山上的,到你门上了,有活自然得先让家里人干了,对不?”宝子嘿嘿地乐着,搂着二军狡黠地说:“看你面子……那咱可当鞋垫子了。”他说完“看你面子,”又故意停顿了一下。
哈哈哈……大伙都笑着,上了楼。
宝子把我们先安置在三楼旅店,说过几天楼上再添置两张空床后,我们再搬上去。哥俩交代我几句,随宝子上五楼办公室及宿舍。我们倦怠地躺在床上,议论着下一步。
“三哥,这宝子长得挺凶,不像好人,跟着他咱们会不会吃亏?”阿四不无担心的问。加成跟了一句说:“他那个坏样子,很像我一届的技校同学,经常打架、欺负人的那个。”
“听他的大名,他哥应该是我老丈人家邻居,恍惚记得听他哥说:威海有个弟弟。”大力闭着眼睛,努力地回忆着。
“如果你们都能和他套上关系,咱们的活肯定能多点。”我感慨地说,“有点关系就好说话,到哪不都讲究这关系网吗?”
阿四接口说:“光有点关系顶个屁用,现在的人多势利,你没有利用价值,亲哥俩也不见得近。”阿四顿了顿,“还得看三哥家亲戚,两辆轿车往这一开,再加上光腚娃的身份,咱们只能跟着三哥借光喽!”
我摆弄着手机,边打字边说:“不能光靠这点关系,事在人为,主要还得看咱自己的表现。过几天咱们安稳喽,看看实在不行的话,给宝子买条烟或请他吃个饭,不花钱到哪也白扯。”
加成坐起来,拿着遥控器不停地换着频道,慢条斯理地说:“走一步看一步吧,不能盲目地投资。你们刚才注意到没?宝子好像出事了,等着大军出面摆平呢!”
“看宝子的神情,好像是那么回事。”我们几个都猜测着。
“当——当——”听到敲门声,加成起身打开。
“姐夫怎么样?”大军二军进门就问。
我急忙坐起来,招呼他俩坐下:“你哥俩介绍的地方,肯定错不了!”
大军说:“姐夫,你们在这先干着,如果不如意,咱再回烟台,大不了俺哥俩再来接你们。”
“可别,不行就回家了,咋好意思再麻烦你哥俩。”我心里寻思,这份人情可大了,以后咋还人家呢?
“就是,这次的事,俺哥几个就够不好意思的了。”
“你兄弟俩又是饭店,又是开车地送,等有机会回东北,一定好好请请你哥俩。”哥几个你一句我一句地客气着,感谢着。
大军又点燃一根烟,站起来说:“姐夫,我再交代你们几句:威海人特别排斥东北人,干活时尽量别跟人家发生口角,能忍则忍。当然,人家骑在咱头上,咱也绝不轻饶。”
我站起来说:“放心大军,俺几个都是本分人,长这么大,还不曾与人动过手呢!”
二军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有些遗憾地说:“这不,宝子让手下干活的两个东北人,把一个当地人打坏了。其实也没大伤,可人家张嘴就四万。不交钱,公安局立马就抓人。宝子现在去医院交两万,那还是我哥刚才打电话找人托关系,要不四万必须一起交。那两万等俺哥俩回家,给他打过来。两万晚交一天,就得搭这么大个人情,就别提免一分钱的事了。总之,看在钱的份上尽量别和人家动手。”
我们几个面面相觑,低下头去,默然不语。
我心想:四万块钱我们辛苦一年也未必挣来,人家就这样不疼不痒地打了水漂,难道只为出一口气?
“放心吧,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们哥几个身上。”我们几个都说。
干了几天,大致了解了一下这里的状况。楼上十多个人,其中有两个小头头,早八点以前,宝子没到之前,一般由他俩往下分配活。那两个小头头我们也见到了,就是打人的那俩,也并非三头六臂。一个瘦的小脸一条条,威海的海风比较大,如果他立在风口,肯定刮得他像孙悟空那样在天上直翻筋斗。鼻子好像不透气,不一会儿就哼一下,大伙戏称他叫“哼将军”。另个胖的坐着都呼哧带喘的,没要紧事从不下楼,买烟之类的事,都是指使屋里的小随从。只要头一挨床立马呼噜声就起,而且还与众不同,他是张着嘴往外哈气。于是,人们笑虐地称呼他“哈将军”。他俩手下有三个直系的人,一起在屋里做饭吃,宝子中午和晚上则和他们在一起吃,偶尔,老婆孩子也来。其余的人,只能插空偶尔做饭而已。活先到他俩手里,像沟北的方便面,沟南的洗衣粉,这样即轻松又挣钱多的活,当然哼哈二将留给自己人了。像一大早,润丰玻璃这些地方,都是饮料、八宝粥之类,包装纸盒相当地滑,抓也抓不住。即难卸又要码高垛—垛高至顶棚。而且库房离车远,卸货用的是小推车,一趟只能装十多盒。总之,各个环节没一处占优;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没一样齐全。挣得少而且又相当的累,同样的一车货,如果在别的货站,至少能提前两个小时。老板只按价格,不理会时间。几百平米的库房,货堆得几乎没有下脚的地,然就是这腰缠万贯的老板,可能知道工人有的是,即不花钱买大推车,也不舍得在门前好好修修路,却还跟我们打工的计较几块几厘的价钱。想想近代的地主也不过如此而已。宝子看重的只是总钱数,他不管去多少个人干和干多长时间,在他的心里永远都清晰地记得一百块钱里有他二十块钱。
像这样类似的活只能分给我们这些新来的和屋里那些小随从了。
阿四他俩铁了心地回家,不仅嫌现在是淡季,挣不了几个钱,更主要的是不愿意让他们剥削。看见宝子和那些老板们的嘴脸,心里就不舒服,而且气愤难当。剩下加成我俩孤零零的,顿觉失去了依靠。临走,我们四个一起去海边公园玩玩。出来有半个月了,我们都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看海。
在烟台海就离我们几百米远,我们没一个好奇地去看,光想着挣钱了。
进了公园,感觉这是个海湾,宽敞的沙滩,水静静的没有一点波澜,远远就看见一条甬道直通海中央。我和大力、阿四直奔甬道,想去海中央看个究竟。顶数加成年轻,而他却靠着岸边一个制高点不动了,并说:“有啥看的,我等你们。”平常从不玩手机的他,此刻,旁若无人地玩起了手机。我纳闷了,平时只要有空,我手机几乎不离手,此时,我都放眼大海,他怎么反而钻进了手机?
加成不愿回家面对苦瓜儿脸的老婆,因为经常地舌战,他的心早已寒到了脚趾丫,对天下所有的女人都不感兴趣,什么歌星、影星、偶像派、***派,只要跟他提,他不但不屑听,而且还要跟人急,认为没有一个好东西。出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与家里通过一次电话。他明知道回家上山去捡松子,肯定比在威海挣得多,但想起东北冰天雪地,死冷寒天他就打怵,哪里更艰苦,他心里清楚得很。虽然加成时刻不忘自己有一双胞胎儿子,都在外地念高中,花销很大,但也愿意留下来享受一下威海高质量的环境和气息。用他自己的话说:自结婚以后,还从没卸下来夹板喘口气哩。
我和他不一样,虽说今年姑娘刚考上伊春一中,过几年,姑娘念完大学,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困难只是暂时的。跟老婆在山下陪读三年了,捡松子必须得回山上,我不愿意回。以往,竟我一个人在山上早呆够了,永远也做不完的饭,永远也洗不完的碗;烧炉子,打水,那么多琐碎的活,哪一样不干能行?烦死了。虽然,老婆一再打电话来说:她去了伊春当保姆连陪读。再三地劝我不行就回家,她挣钱养我,还说结婚这么多年了,也该她放放光了,让我在山下呆着就行。我怎么好意思呆着,我也是堂堂七尺汉子。威海的空气质量好,温度适宜,好容易遇到这样的好地方,我才不回呢。再说挣点是点。虽说现在是淡季,过些日子肯定会好的。我就这样坚信着。
甬道不是很宽,是用巨石铺平的,有时,海水能扑打上来。两边都有年龄不等钓鱼的人,游客们不知是应该看海还是应该看他们钓上来的鱼。小桶里装着刚钓的形态各色的鱼,游客这个问完了,那个又来了,钓者便爱答不理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海里漂浮的鱼漂。我眼望着深海,除了看见微微涌起的波澜,其他什么也看不见,我感到一阵迷茫,就像此刻茫然的心情。站在海中心,抬眼看对岸,高楼大厦,比比皆是,虽然近在咫尺,却像幻景中的海市蜃楼,可能永远永远都遥不可及。
一转眼,又找不到阿四了,那小子比我小一岁,仍旧上蹿下跳的,没一刻安稳,在哪都呆不住,这又不知道跑哪去看奇景了。
阿四的姑娘今年考上的大学,两口子都能干,感情挺好,家里不算缺钱。前些年,阿四上树猛得狠,好像没有上不去的树,而且上得快,在树上打得也快。每次秋收,他家都是林场的佼佼者。一连几年,她家收入颇丰。九八年的时候,松子又迎来前所未有的大丰收,松塔压得枝头弯弯着,阿四恨不得不睡觉,就想把山都搬家去。由于心急,在树尖上撅塔子时,一个疏忽,树头不经意被他弄断,他都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掉到了地上。他傻子一样搂着树头坐在藤条里。
在家休息了几天,感觉没啥大碍,疯了一样继续上,想把歇的这几天的损失在瞬间夺回来。老婆怎么说都不听。那年,他家的收入仍在林场名列前茅。几年过去后,又一次大收,他摩拳擦掌,再展身手。打到中后期,再一次从树上跌了下来,所幸,这次依旧无大损伤。从此,老婆绝不再让他上树。不打松子,木耳菌就做得量大。今秋,他再也忍受不住诱惑,又一次冲进山里,由开始慢慢地上树,逐渐地恢复年轻时的风采。林场的人都竖大拇指称赞他的坚持和坚强。如果不是临结束时,林场连续掉下来两个(一死一重伤),恐怕他是不会跟着我出来的。如今,他回家可以领着老婆去捡松子,两个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要强大得多。外加上热炕头热被窝的,天天可以卿卿我我,干嘛不回家。
大力比我略小,十几年前,一家三口去了山东枣庄,在几个姐姐的帮助下,开了个熟食店,生意很火,规模不断地扩大。受当地人男尊女卑的想法,一门心思想生儿子。由此可见,入了乡就得随俗啊!不久,老婆挺起令他骄傲的大肚子。恰巧,东北老爹孤零零的需要照顾,他只好变卖店子,回东北生儿子了。天随人愿,老婆很争气地生了个大儿子,大力乐—乐得一时找不到北。
如今大姑娘上大二,小儿子刚上初中,为了养儿子,他已是满头白发,像个爷爷。他总说:“有儿子就是自豪。”
加成听了反驳说:“有啥自豪的,你多买一栋楼,我多买两栋楼而已。”
呵呵,大力先乐后说:“那能一样吗?他们不买楼的,钱也没剩下,全搭姑娘了。咱买楼的,最起码添个孩子跟咱自己一个姓。如果你运气好,两个儿子又都随你,你就有四个孙子接户口簿。别人家的失传,你却反过来择优录取。”
噗嗤,加成也被逗乐了。
他也搬到山下陪读,他回家也不能去捡松子,山下的冬天没什么活可干,不明白他着急回家干嘛?
我和大力回来寻到加成,问他阿四呢。他木然地摇摇头,把手机放进兜里:“光摆弄手机了。”随即,加成又说:“你们听。”悠扬的音乐随着海风飘过来,细听是萨克斯吹奏的《最炫民族风》,我最喜欢的歌曲。
“兴许阿四去了那里?”我和加成齐声说。
我们顺着沙滩一面浏览风景一面欣赏音乐,动感的节律,时刻震撼着我。近了,音乐是从一个凉亭里传过来的,里面坐着的、站着的、围着不少人。莫非是卖狗皮膏药的?现在摆地摊的都好用个录音机放着流行音乐,招揽过路的人,我这样想着。我们快步奔过去,看见了阿四的背影,接着看见一个老者上下左右摇晃着,喔,音乐是他吹出来的。
我们拍着阿四的背:“你小子怎么先窜了,找到好地方也不打个电话,只知道自己独享。”
阿四嗯啊地不知所措:“……快看演奏吧!”
老者一下一下地翻着曲谱本,拿着萨克斯按按这个键又按按那个键,好像在调音节。鼓捣一会儿,吹起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熟悉的旋律在心间飘荡。细听再细听,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只是调一样,有很多地方不是稍稍走音就是没投入感情,总之交汇的不好。虽说我不懂音乐,但我能听出很多的瑕疵。我在想:如果我写小说,什么时候都能把自己的感情,人物的感情融入到字里行间,那就好了。
可我又在想:看见老者依着朴实,又得依靠乐谱,才知道他是个初学者,可为什么在远处以为是录音机里放的就听不出瑕疵呢?
看来有时候:近观没有远听的效果美妙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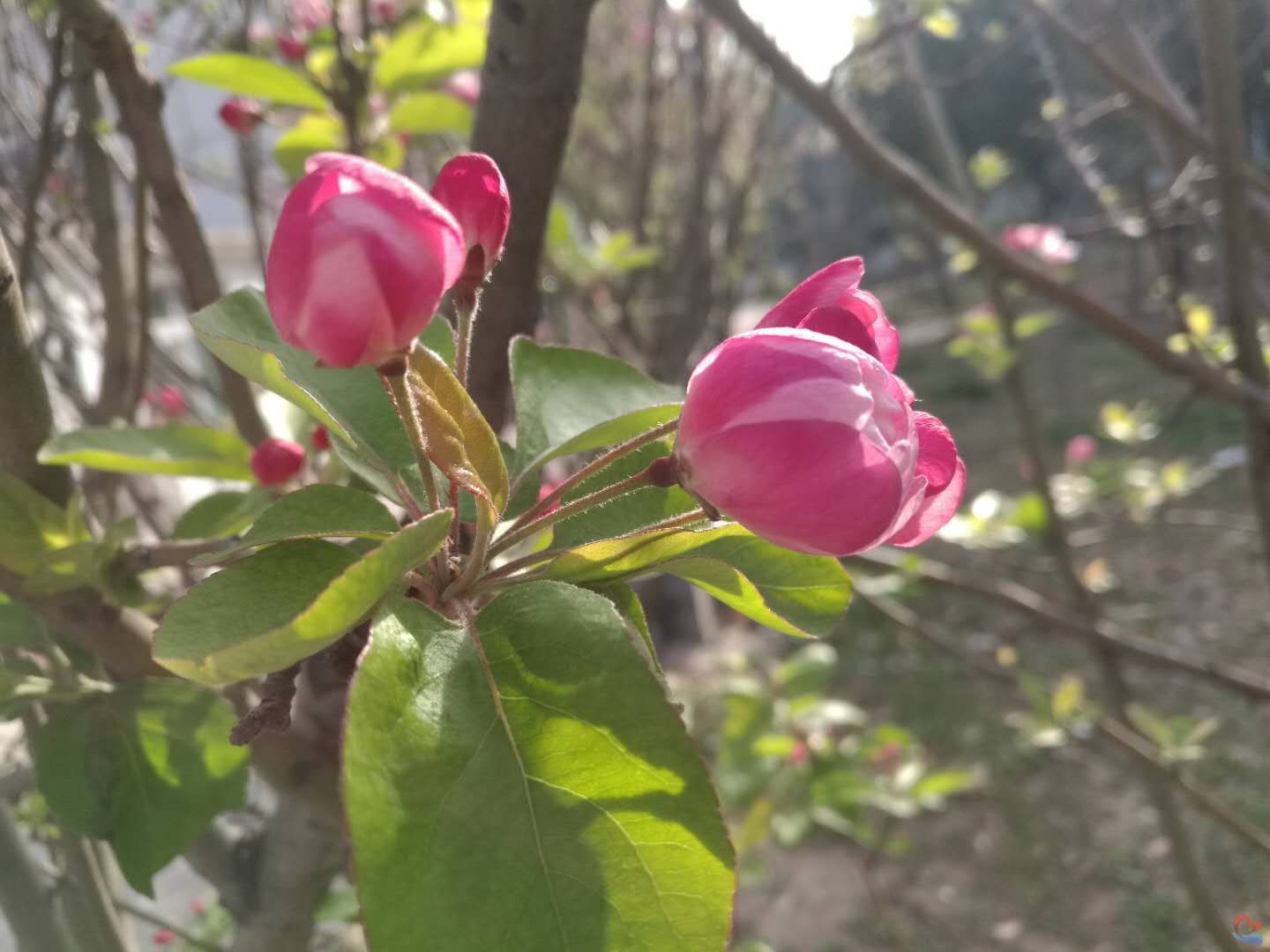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