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TOP | |||
|
蚂蚁
管理
作者:曹含清 发表时间:2024-06-25 14:35:38
评论:0条
关注
编者按:蚂蚁,为典型的社会性群体,就如人类社会,具明确的社会劳动分工形式。因此就有了许多与人类的相同之处,自食其力,默默无闻;不知道是人类抄袭了这些生物的生存模式,还是这些生存模式并不为普罗大众所独有;总之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还有听天由命之生老病死,除了富贵在天会成为宿命论中的必然,就剩下努力了命运才会把握在自己手里的渴望。不过人们始终还是相信自己的命运就被老天操控着,我们的努力根本就无法将自己的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该是有多么地悲观。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命运,究竟是被所谓的神明所操控着,还是我们自己明知道天会有不测风云,人有会旦夕祸福这种必然,却依然选择将被动视之为安然的无奈。作者笔下的人间有生命之无可适从,有生存与生活的光阴如梭;就像一幅素描,其中的亲情温馨与人情冷暖都有值得珍惜甜美,也有任他风雨飘摇,我自临窗独沉吟之豁达。推荐阅读! |
|||
|
四妮的身体急剧消瘦,心情糟糕至极。她吃不好睡不好,眼眶塌陷下来,干枯的脸上布满愁云惨雾。她常感到头晕、胸闷,走起路来软绵绵的,做起饭来也会气喘。她支撑不住,就去村子的卫生所包了些药。 村医王虎询问一下情况,望了望气色,以为她是因为莉莉的事情肚子里胀满了气,就开了些舒肝顺气的药。 老罗的腿脚远没从前利索,感觉精力被榨去一半。他骑上三轮车赶集卖腌菜,站了大不一会儿感到腰酸背疼,就连旁边的刘屠户和老孙都能看出他的身体孱弱不堪。 “老哥儿,你这大半辈子啊,被你大儿子坑惨了——早些年给他结婚出了很多彩礼,搞得倾家荡产。这结婚后大儿媳妇儿不是省油的灯,勾引来野男人揍你一顿,瞧这打的,我看你身体大不如以前喽。” 刘屠户说着把几块大骨头送给他,说是大骨头滋养身体,让他回家后熬汤喝。 “过段时间就好了。”老罗咧着嘴说。 老罗回家后看到四妮身体的衰颓很伤心,他以为她是因为生气所致,气大伤身,毕竟儿女连心,她恼恨莉莉,又操心卫东的未来。他劝她想开些,不要生气,儿孙自有儿孙福,不必为他们过多操心。话虽这样说,道理全明白,但是她看不开,他也想不通。当小勇睡着后,蛐蛐在屋角鸣叫,他的怒气又会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不由得在黑暗中骂几句。 四妮在厨房忙活很久,颤颤巍巍把饭菜端上木桌。老罗瞅着陪他大半辈子的老伴儿,觉得老伴儿好像一下子衰老二十岁!有些事情真的比尖刀犀利,我们触碰到它们就丧魂落魄! “包的药效果不行吗?” “还会感到胸闷,浑身上下没力气。做一顿饭花好大的功夫。” “要不给卫星打电话,让他明儿个回来带你去尉东医院检查一下。” “不用麻烦他,他在工厂很忙。等我吃完了药,过两天再看看。” 她本想忍耐两天,更不想麻烦儿子。当要麻烦儿子时,她顾虑重重,担心耽误儿子工作。她好像轻如鸿毛,儿子重如泰山。 卫星打来电话询问他们身体时,他们总是说身体还凑合,他们不想让儿子操心。 然而当天晚上病魔潜入四妮的体魄,死神突然降临! 傍晚,猫头鹰在村子的老桐树上啼叫,咕咕喵,咕咕喵,一叠连声,叫声瘆人,好像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半夜时,村庄一片死寂,仿佛沉陷在深不可测的海底。四妮突然被一阵疼痛击醒,她的胸中如刀绞般的疼痛。她挣扎着身子,粗喘着喊醒老罗。 老罗摁开电灯,只见昏黄的灯影下她大汗淋漓。她的手颤抖着捂在胸前,疼痛已让她的身体扭曲。 “胸疼,喘不过气……”她呻吟着说。 “你忍一下!” 老罗从没有这么惊惶。他立马给卫星打电话,卫星吃了一惊。 卫星赶紧拨打急救电话,穿上衣服下了楼。 四妮被急救车送到医院后,老罗和卫星站在急救室门外焦急地等候。 “你给卫东、卫兵打个电话,通知他们过来。我看你妈这次病得很严重。”老罗神情忧伤。 “给大哥打了,他上午能回来。二哥的电话打通了,没人接。” 天色渐亮,曙色如水在大地上流淌。 急救室的门开了,大夫表情凝重地走出来说:“我们已经尽力了。病人患了急性心肌梗死,现在生命体征已经消失。你们回去准备后事吧。” 四妮没有被抢救过来,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她的生命之光猝然熄灭! 老罗和卫星像是被雷霆击中,感到天旋地转。他们痛哭流涕望着四妮的遗体,一切如一场噩梦。 四妮的遗体被运回家时太阳已经爬到半空,白花花的阳光铺在地上,一群麻雀在喳喳的哀鸣。 院子里来了一些窜忙的乡邻乡亲,大多是中老年人,等着老罗安排葬礼的事情。 老罗坐在四妮的尸体旁,他的泪水像是决堤的河水从眼窝流出,他浸没在悲恸中。他抹掉眼泪,捋了捋思绪,依循芦湾的风俗,停尸三日出殡,向亲戚故旧报丧,采置孝衣孝布及寿木,预定纸人纸马及冥楼,雇请厨子和唢呐队……至于费用,老罗拿出所有积蓄,卫星也拿出很多。安排妥当后各忙各的事情。 卫东中午时才回来,跪在地上扶着母亲的尸体痛哭。 卫星向卫兵打了好几通电话均无人接听,午后又打了一通,这次卫兵终于接听。 卫星泣不成声地说:“二哥,咱妈没了。” 电话里传来卫兵淡淡的回音:“我在上海出差,这一两天回不去。” 报丧人去县城向林家登门报丧,傍晚他回来时鼓着腮帮说:“我已经通知林富友,正巧碰到卫兵在客厅坐着。他说自己很忙,等他妈出殡时再回来。” “他不回来也行,我就当没他这个儿子!等我死时,你们别通知他。”老罗悲愤地说。 原来那天半夜卫兵被手机的铃声吵醒,他起床揉着睡眼瞧了瞧,是卫星打来的。彩霞也醒了,她坐在床上胡乱臆想说:“卫星这么晚打电话,准是有急事——要么是急需借钱,要么是你爸你妈被送进医院了。不管是啥事,对你都不是好事,你爸你妈住院,你去的话是要分摊医疗费的。要是他们死了,你要躲得远远的,不然你还得分摊丧葬费。以后你家这些破事儿你别瞎掺和。” “老婆,还是你想得周到!”卫兵把手机调为静音,又躺在床上酣睡。 四妮出殡的前一天发生两件令老罗头疼的事情。 罗家的祖坟原本是一片荒地,后来村干部把那片土地承包给赵老五,赵老五在空地上种下庄稼,那时玉米的青苗长了四五寸高。老罗带着几个族人去看墓地,准备勘定四妮墓穴的位置——这样需要毁坏一些青苗。他找来赵老五商量,赵老五开口要价三万元,并且说了一串前例,比如上个月孙榔头他妈死了,孙家的祖坟在王留德家的农田中,挖了一个墓坑,王留德向孙榔头索要三万块钱。 “你不拿出三万块钱,就不要把人埋进祖坟!”赵老五绷着脸,义正辞严地说。 老罗一筹莫展,哪能拿出这么多钱呢!他已经把压箱底的钱掏出来了。卫星手头不宽裕,也拿出一笔钱。卫东每次回家把钱交给莉莉,莉莉已卷走所有存款。卫兵装作缩头乌龟不露面,要躲到天涯海角去! 老罗又想到自己距离死亡越来越近,等他死时也将遇到同样难题。这个难题无疑将抛给儿子。他果断在自家田地选定一处位置作为四妮的墓穴,当他在田地干活儿时也能陪着她。因为村子也有这样的先例,族人无人反对。 墓穴选定后又冒出一个令人头疼的事情。墓坑约两米深,挖掘土量较大,需要好几个年轻力壮的人。来窜忙的那些乡亲们大多年老体衰,力气不足。老罗找遍偌大的村子,只找到两三个身体强壮的人,无奈之下他只好让卫东、卫星也去挖墓坑。在芦湾,儿女为自己去世的父母挖墓坑原本是有所禁忌的。 到四妮出殡那天,天气燠热,村庄像是一个蒸笼。唢呐声声,笙箫悲鸣。临近中午时卫兵戴着孝布跪在灵前干嚎,卫东、卫星对他不满,众人看得出他在装腔作势假哭,也没人劝他起来。 当四妮的棺材埋入泥土时,夕阳已经落山,血红的残照流泻在土坟上,焚烧的纸扎、纸钱在坟前散着余烟。田野的尽头升起一层暮霭,托起一条模糊而粗犷的地平线。 亲友们纷纷散去。老罗让卫东、卫星先回去,他想自个儿坐在坟前呆一会儿。 老罗回想起四十多年前他和四妮结婚时,她的笑脸像花儿一样。后来她为他生下三个儿子,尤其生卫星时受了很多苦,因为超生,她挺着大肚子四处辗转。 “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扎在他的脑子里。他很少自己洗衣做饭。对孩子他几乎放任自流,除非他们犯错,他会打他们的屁股。 家里的细务琐事他全交给她处理。他脱掉脏衣服,让她洗。他从田里回家,让她把热饭端上木桌。他很少关心孩子,只是看着四妮给他们喂奶、洗屎布。儿子们像是三棵小树似的嗖嗖长高,横生枝节时他顺手砍掉。 记得每当儿子生病时,是她最焦心时,有好几次深夜她独自抱着发高烧的孩子去找村医打针,还有两次冒着滂沱大雨。 她苦了一辈子,没有享福。她操持大半辈子把儿子们养大,又看着他们结婚生子。没想到他们像是债主,有还不完的债,总不让她省心。 如果把她的生命像蛋糕一样切成八份,儿子们占有五份,丈夫占有二份,留给她自己一份——她大部分是为儿子和丈夫活的。 她是家的台柱子,她为这个家无私奉献了太多。 家,是我们相依相伴的地方,不管谁离开,就会少一份力量,少一份温暖,少一份光亮,家就会残破不全。 当我们都离开,家就不存在了。家就成了坟。 暮色像洪水一样淹没田野。夕阳被埋入地平线之下,被黑暗噬食,次日它将浴火重生。焚烧的纸扎、纸钱烧成了一堆灰烬,弥漫着一丝丝刺鼻的味道儿。 老罗用一只手掌撑着瘦而干瘪的身体,他挣揣身子站起来。他的眼睛像是一口幽黑的枯井,瞳孔没有一丝亮光。 “孩子他妈,你累了大半辈子,你就躺在地下好好歇息……我先走了。”他缓缓离开坟地,喃喃自语。 接下来的日子老罗慢慢习惯孤独,慢慢应付生活的烦琐和悲楚。 他和四妮磕磕碰碰生活四十多年,每天在平淡的柴米油盐中盘转,两人没有过多的恩爱,更没有风花雪月的浪漫。两人偶然还会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拌嘴。她死后他感到自己除了悲伤,便是空虚——他好像已经死掉,魂魄随着她去,留在人间的不过是一具没有腐烂的臭皮囊! 他愁闷时多么希望再和她唠几句,或者拌几句嘴也好,然而她已不在,四周只有冷冷清清的空气。他只好自言自语。 日子被哀伤的阴影笼罩,他好像永远走不出来。当他想起在这世上还有自己爱的人,还有自己爱做的事时,他又会继续努力走下去,慢慢将阴影甩在身后。 是啊,生活需要的不是忍耐与逃避,而是心怀爱意继续走下去。 小勇去上学后,家中只剩下老罗一个人。他无所适从,有时到腌菜屋去瞧瞧那些腌菜,闻闻酱香味儿,他的心情会好一些。他有时独坐在院子中盯着芦花鸡或老桐树喃喃自语。他多次产生幻觉,望到四妮坐在水井旁洗衣服或者在屋内扫地。 阳光撒满院子,燕子在屋檐下飞来飞去。桐树上的蝉声稠密而冗长,吱吱的叫着。 老罗坐在木凳上,低头盯着斑驳的地面,只见一群乌黑的蚂蚁绕着一块蒸馍碎屑忙碌爬行,它们使出浑身力气撕拉,要将碎屑搬运到墙角的蚁穴。它们挪动的速度极慢,比不上太阳在天空移动的速度。阳光将一片树影儿遮在它们身上,又慢慢把树影儿移走。 它们虽然身体渺小,力量微弱,但是它们勤劳勇敢,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劲头儿,要将“巨大”的碎屑搬回家贮存。 老罗揉了揉干涩模糊的眼睛,望到那些密密麻麻的小生命在眼前奔忙,挑不出一个偷懒耍滑的,更挑不出一个钻营投机的。它们微小的体内仿佛澎湃着伟岸而正直的力量。 它们的劳苦在人们看来似乎微不足道,它们仅仅是为了获得食物的碎屑!这些东西是人们所抛弃的,所不屑一顾的,但是却是它们所珍惜的、所梦寐以求的。 它们忙碌一生,仅仅是为了吃口饱饭,不挨冻受饿。 在生存面前,人们和这些蚂蚁是多么相像啊!或者说,人并不比蚂蚁高明多少,不比蚂蚁伟大多少。 老罗想到这些,感觉自己在大地上也是一只蚂蚁。 小勇放学后,背着书包弯腰凑到老罗跟前问道:“爷爷,你在干啥呢?” “看蚂蚁。” “蚂蚁在搬家吗?” “不是,在搬运吃的东西。我问你,蚂蚁几条腿?” “当然四条腿!” “你仔细瞧。” “呃,我数数……六条!蚂蚁六条腿!” “还有啥动物六条腿呢?” “呃……我想想……鸡、鸭、鹅两条腿,猪、狗、猫四条腿,啥六条腿呢?我不知道。爷爷,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你抽空逮只蜻蜓和瓢虫瞧瞧。” “爷爷,你带我去逮蜻蜓吧!”小勇兴趣勃发。 “我要做饭了。” “做啥饭?” “面条。” “唉,天天吃面条,我真的吃腻了!” “其它饭我真不会做。” “要是奶奶活着该多好,她会做很多饭菜。” 小勇的话刺激到老罗,他面露愧色,心想自己确实该学习烹调了,学会做几道拿手好菜,到春节吃团圆饭时也能派上用场。老伴儿不在了,还能叫团圆饭吗! 老唐知道老罗心里难受,时常来串门唠嗑儿。 当时老唐遇到一件烦心事无处排遣。他的女儿盼盼远嫁湖南后很少和他联系,如今他年老志衰,欲望消退,已安于孤苦伶仃的生活,不再去找姘头胡混。他的两个侄子竟然盯上他的宅基地和田地。一个侄子提出让他搬入自己家的柴房住,便于朝夕照顾他,当然他的宅基地要归侄子所有。侄子已向他说过多次,还草写一份协议让他签字画押。另一个侄子看上他的两亩三分地,要每年给他五袋麦子,足够口粮使用,让他停止劳动,安心养老,不过他的田地和一辆破旧的拖拉机要归侄子所有。 老唐向盼盼打电话商量,盼盼对他不闻不问,漫不经心地说:“你爱咋办就咋办,不用给我说。”然后挂断电话。 他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心里盘算他搬入侄子家后自己病倒在床上有人帮他喊来大夫,不至于尸体生蛆而无人知晓。弊处是寄居在侄子家像只燕子,要看侄子的脸色行事。他的宅基地如果转让给别人,按照村子的行情,大概值三四万块钱。他又担心侄子会转让给别人。如果有一天侄子寻事赶他出门,他将无家可归。 他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时常腰酸腿软。他从前种一些棉花、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它们费时耗力。如今只种麦子和玉米这些“懒庄稼”,一年收两季,无需太多体力。他夏收二十袋子麦子,秋收两千多斤玉米,留足口粮后剩余的全部卖掉。这样一个人吃穿不愁,偶然还能买一只烧鸡配上一瓶白酒。 仔细盘算后,老唐不想将宅基地和田地转让给两个侄子,可是担心得罪他们,将来自己死后无人料理后事。 “你还记得朱老兵吗?”他问老罗。 “当然记得,他比咱们大十来岁,已经死了七八年了吧。” “嗯,他死去整整八个年头。近些年我常想起他,有时做梦还梦到他。” “为啥?” “我记得他死后好几天才被人发现,尸体腐烂,身上爬满蛆。他的几个远房亲戚没人管,李正祥找人把尸体裹上竹席连夜埋进果树下……那天我帮忙把臭烘烘的尸体扔进土坑,拿着铁锨挖土填埋……八年前我身体比现在好得多,真是岁数不饶人啊!我担心我死后的下场和朱老兵一样凄惨。” 朱老兵是一个老鳏夫,是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儿。他无儿无女,只有几个关系疏远的亲戚。他离群索居,常年住在苹果园的小屋里。村里人几乎无人和他往来,他仿佛活在人间的边缘地带。 八年前的夏季有一个人内急,脱下裤子蹲在苹果园的草丛中大便。大便后发现口袋没带纸,他向着繁叶荫庇的小屋高喊朱老兵,想借用两张手纸。谁知道喊破嗓子没人回应。他抓来一把树叶应急。他提上裤子走向小屋,一股恶臭扑过来。他一阵惊疑,捂着鼻子推开门望到朱老兵蜷着身子躺在床上,身上爬满蛆虫!谁都不知道朱老兵到底是啥时候死的,估计着已经死了好多天。他万分惊恐,赶紧跑回村子喊人。 朱老兵的那几个远房亲戚装聋作哑,根本没人照面,更不会有人出资为他买一副棺材。村长李正祥走遍全村,喊来几个中老年人用铁锨在果树下挖掘一个浅浅的墓坑,然后用竹席和床单包裹上尸体,让人抬入墓坑掩埋。 老唐每想到这件事总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毕竟自己和朱老兵一样是老鳏夫! “你住在村子里,没住在果园,不会有那样的下场。”老罗安慰他说。 “老罗,你要是三天没见我出门,求你来敲敲我的门,我担心我死在屋子里没人知道!”老唐说着,嘴巴颤动一下。 “你别多想。” “我啊,今儿个想清楚了。我看透两个侄子的小算盘,对我没安好心。他们想要我的宅基地和田地,没门儿!我呀,准备明儿个去买副棺材,再把一瓶农药放在床头。要是我哪天生病下不了床,我就喝下毒药,两脚一伸死掉。到时候啊,还得麻烦你们喊人把我装入棺材。我不要穿寿衣,平时穿啥死时就穿啥。我拿不出三万块钱,把我埋到自家田地就行。找不来有力气挖墓坑的人,还得麻烦几个老哥儿亲自动手,墓坑不用挖得太深,能盖住棺材就行……” “老唐,瞧你说的!你现在好好的,别说这些丧气话。”老罗说着想起已逝的四妮,内心不免一阵悲凉。 “咱们到这个年纪,活一天少一天,哪天说没就没了。我再啰嗦几句,我床下的红陶罐藏着我积攒的几千块钱,等我死后你们要帮我请来唢呐队,必须要请歌舞队。我啊,最喜欢看歌舞队长相漂亮的姑娘,我死时还想再看一回,也不枉披着人皮在这世上走一遭。” “你这话说的,说不定我比你死得要早。” “我等一会儿再去向老蔡说说,你俩总有一个比我走得晚吧。” “哪真不一定啊!” 老蔡这些年过得很不如意。他辛辛苦苦盼到军伟大学毕业,本想自己可以松劲歇脚了,没想到肩头的担子越来越重。 军伟大学毕业后在兰州一家机械厂工作,成为车间的技术员,薪资并不高。他在工作中认识一个驻马店的姑娘,两人作为河南老乡很谈得拢,很快陷入热恋。 老蔡十分高兴,想着双方是自由恋爱,应该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结婚时应该不用出什么彩礼。可是当谈婚论嫁时,女方的父母却开口要十万元的彩礼,并且强调在他们家乡彩礼都是二十万元起步,这已经是优惠到底的价格。 老蔡观望一下四周,发现芦湾的彩礼已水涨船高,大多十万元起步。他斟酌一下,让军伟和女方斡旋,让女方看在军伟是大学生和自由恋爱的份儿上,彩礼能否再减免一些。 “爸爸,你是不是老糊涂了,现在人家已经给咱们打五折优惠了,你还要人家减免,他们是不会同意的!”军伟正在憧憬未来新婚的生活,以为父亲是在有意作梗。 老蔡翻箱倒柜、东挪西借凑够六万元,还差四万元,干脆像是派发任务指标一样分摊在两个女儿身上,每个女儿拿出两万元。 年底时他又卖掉猪圈中未长大的生猪,总算办完军伟的婚事。 日子过得像是堵洪水似的在堵债,堵住张家,还有李家。有过不完的日子,就有堵不完的债。 两年后老蔡已是身心俱疲,整个人像是被巨轮碾压成齑粉,不过天亮后,还得缝缀支离破碎的身体来拥抱生活。 那天晚上军伟给他打电话说:“爸爸,我在兰州买房子了,一套大房子,将来把我妈和你接过来住——但是现在首付款还差二十万,你帮我凑凑吧,至少凑十五万。” 父母像是子女的银行,这家银行不求回报,即便被子女取款直至破产也在所不惜。 老蔡就是这样,一旦儿子有求于他,他不遗余力,决不吝惜。旧账未清新账又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厚着脸皮东奔西走找亲戚朋友借债,又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卖掉,比如碗口粗的杨树、已经使用很多年的洗衣机和电视机。 他又向两个女儿写下借条,各借四万元,这样最终凑齐十五万元。他担心去县城的票车上有扒手,就骑着自行车分为七八次到银行汇款。 从银行走出后他松了一口气,骑着自行车要回家。军伟又打来电话说还差两万多,他无奈地说:“军伟,现在亲戚朋友能借的全借了,家里值钱的东西能卖的全卖了,我真的没辙儿。” 儿媳坐月子时,老蔡的老婆坐火车去兰州照顾。谁知道婆媳不和,两人经常舌剑唇枪、短兵相接。有一次老蔡的老婆将一盆温水端到儿媳面前让她洗脚。儿媳吹毛求疵地说:“水太热了,你想烫死我啊!”她说着,哐当一声,一脚将水盆踢翻,水花四溅。 老蔡的老婆受了气,也受了惊吓,不久她回到芦湾后心脏出了毛病,需要时常服药。 军伟已经连续七八年未回家。他孝心未泯,春节时不忘给父母打一通电话,说村子天气冷,没有暖气,担心孩子回老家后感冒,今年不回去了。即便他挈妇将雏回驻马店岳父家,也绝不顺道拐到芦湾,理由是假期太短,时间不允许。 每年春节时老蔡和老婆常常袖着手站在街角。鞭炮声中望着从城市回来过年的人,他们老泪纵横。他们很想念儿子和孙子! 他们根本不知道孙子的模样,在路上瞧见孩子很亲热,顺口说:“我大孙子应该长这么高了。”有人反问道:“你这些年见过你孙子?”他们当然没见过,心里愈加难受。 军伟每个月需要偿还房贷,还得给孩子买奶粉喝,他常常入不敷出,信用卡刷到透支。他总会将这些艰难的细节传递给老蔡,老蔡听后坐卧不安,想为他分担。 老蔡除了拾掇家里的农活儿,还时常早出晚归去镇上打零工,甚至干一些掏粪的杂活儿。繁重的劳动将他的身体榨得精瘦,活像一只蚂蚁。 老蔡最高兴的时候就是骑上自行车去银行为儿子汇款。他满身大汗,用手掌将几张皱巴巴的钱抚平整递给柜员。柜员对他很熟悉,看到他过来就知道他要汇款。他走出银行舒了一口气,仿佛能够看到压在儿子身上的大山掉落一块石头,至少消减一些压力。 人这一生好像在吉凶祸福之间徘徊,难免会有七病八灾。 一次老蔡在镇上打零工为一户人家抽蒜薹。他在蒜苗丛中挪动身子,两只手像机器一样不断捻着蒜薹的茎向上抽,才能将蒜薹顺顺溜溜抽出来,这样辛苦一天能挣一百块钱。他顶着太阳手脚不停,突然眼前一黑晕倒在地上。户主叫来急救车把他送到医院,原来他患了脑梗死。 他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出院后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的。医生嘱咐他要戒烟戒酒,不能干重活儿,否则有患半身不遂之虞。他刚回家静养两三天,军伟又打来电话说公司效益不好,已经两个多月没发工资,房贷还不上,水电费要交,大人要吃饭,孩子还得喝奶粉,在城市生活哪能缺钱呢! 老罗蹙额颦眉叹息,向军伟叙说自己住院的事情,军伟嫌他啰嗦,根本没有心思听下去,只想追问他能拿出多少钱,也没问他现在病情咋样。 次日天还未亮,老蔡起床蹬上自行车去镇上的养猪场。他虽说身体不如以前,但是喂猪、除粪这些杂活儿还能干得动。 老蔡倒是很羡慕老罗。他向老罗说:“你仨儿子,没我一个儿子花钱多。你现在还清了债,可以安安生生睡觉,可是我欠了一屁股债,睡不踏实,吃啥也不香。” 老罗以为他太溺爱儿子,替儿子过于操劳,直言说:“老蔡啊,你真是把军伟惯坏了,你帮了他一时,帮不了他一世。下次他再给你张口要钱,你直接给他说在城市混不下去,你滚回村子来!” |

|
|||
| 【投稿】【 收藏】 【关闭】 | |||
|
|
|||
| 上一篇:暑假 | 下一篇:风波 | ||
| 推荐美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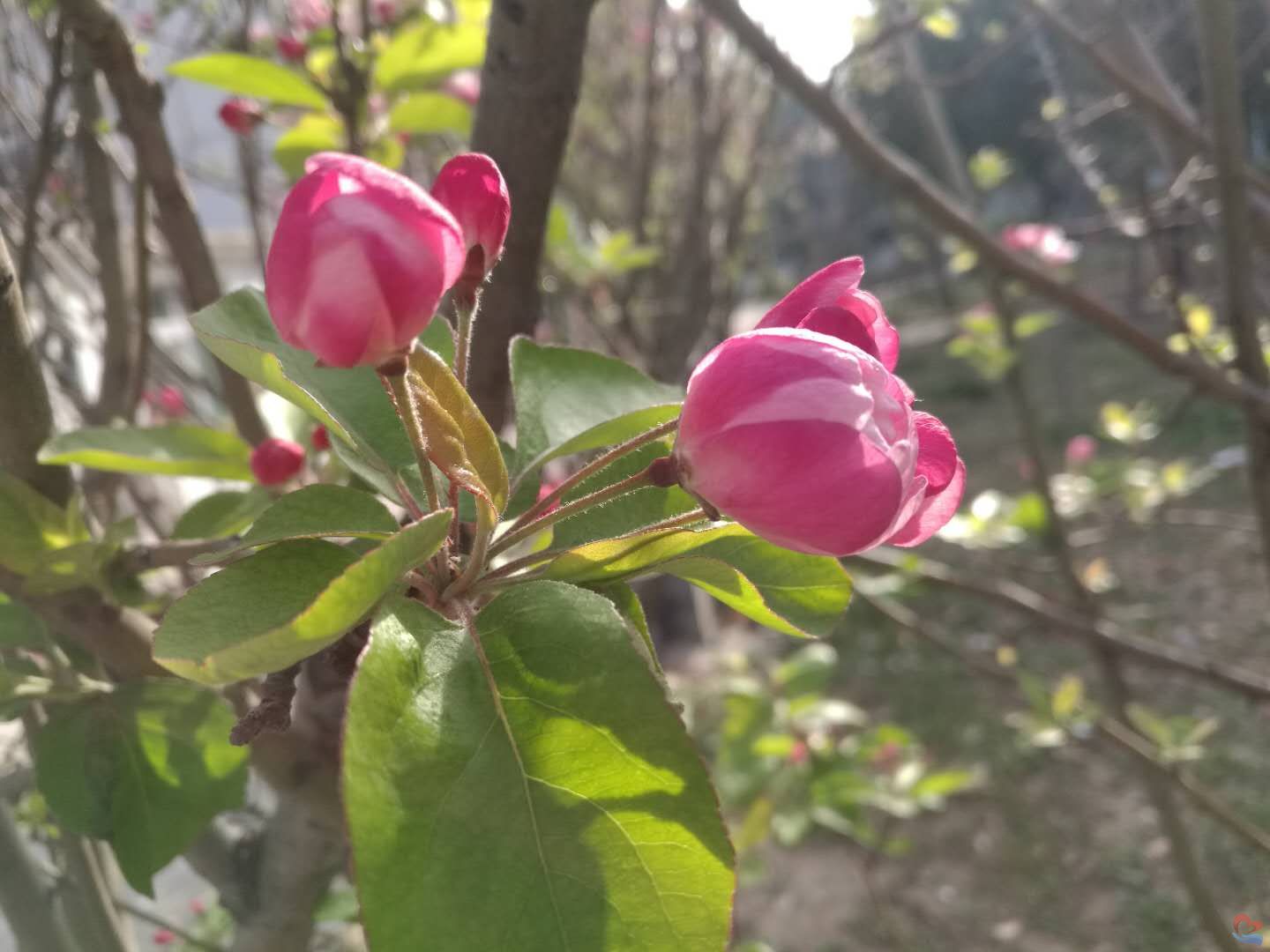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