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斯,长于斯,梦幻于斯的“衣胞之地”,犹如像漂浮于水中央的一张嫩绿的大荷叶,在地图上是很难找到的。前辈们都自豪地或者诙谐地称之为“荷叶地”。有个曾经在我们村,执教多年又懂点儿地理知识的钱姓私塾老先生,他瞧着我们村的居住环境地形地貌,又说我们村像一只头朝南浮在青悠悠清澈见底水面上的大乌龟。他说得很形象靠谱。南首的庙宇,像乌龟的头,延伸至村北的大路,像乌龟的尾巴。东和西村落边缘上散居着的房屋院落,又像是乌龟的左右两只爪。
我们居住的这个“荷叶地”,杂姓并不多。以苏、徐、万三姓,和睦相处于村的东南西北中。而又百分之八十向上的人家姓苏。所以也就靠船下篙,取名“苏家舍”了。庄子不大,人口几百。说得夸张点,村东头烧的肉香味,村西头闻得着。村内大小河流若干,村外河水缠绕,绿树成荫。在兴化县城的东北部,距县城约50公里之多。上世纪交通欠发达的六七十年代,出了门,便见河,想出庄,必坐船。船,成了当时的首要交通工具。离了船,寸步难行,与世隔绝。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只有冬天的村庄显得单调而乏味。眼前呈现的好像永远是灰色的: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树木,灰色的土墙,灰色的茅屋,灰色的土路……唯有到了春天开始,水是绿的,天是蓝的,云朵儿是白的,庄稼是绿油油的。风悠悠地吹,送来缕缕花的芬芳。小鸟唧唧啾啾,落满庭院和树顶,鸽子在屋脊上“咕咕”地叫着,梁上燕语呢喃,伴我入梦。草长莺飞的旷野以优美恬静的环境给人以美的享受。这才是大自然恩赐于我的祖辈们的一份厚礼。在落日余辉的映衬下,展现在乡亲们的视野里的永远是那一柱柱一片片一缕缕袅袅升腾的炊烟,犹如画家笔下的一幅自然美景的彩墨画。村庄人的相处,融洽和睦。一家有难,众人相助。小孩抽筋了,妇女生孩了,老人有病了,众人出钱出力出主意。看到相安无事,大家才会松了口气。只是一到了深夜,整个村庄显得清冷漆黑。有时从睡梦中某个角落,偶尔传出一两声“汪汪”的狗叫声。
走过村东的一座小木桥,便是一片庄稼地。抬眼望去,一条宽阔的南北向的“雄港河”就在眼前了。河面宽六七十米左右。河上没桥。河的两岸,专为防洪排涝而修筑的高二米,宽六七米的沙土圩子。土圩上,长着一种叫“丁子槐”的树木。河岸边,挨水的地方,密密匝匝长着茂密的芦苇。有的斜在水面上,是鸟儿们栖身的乐园。夏天,我们常能掏到很多种大小的鸟蛋。大如鸡蛋,小如花生米,周身浅绿并斑斑点点。拿回家准能美餐一顿。对岸是望不到尽头的田野,除了冬天被皑皑白雪覆盖,便是绿油油一片。小时候,在夏天我常见胆大的伙伴,游泳至对岸,偷些能吃的东西。所以,那边相对而言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诱惑。特别是夏天的晚上,“咕哇咕哇”的蛙鼓声,此起彼伏,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某年夏日的中午,大概我也就只十几岁吧,诱惑超越了我的胆量,我游过了这条大河。上岸,竟发现堤圩下有一“A”字形的渔棚子。我猫着腰,轻手轻脚走近渔棚的门前。有种“柴门半掩寂无人”的感觉。不料,竟惊动了里边的一位70多岁的看瓜老人。花白的银发,满腮的胡须,却一脸的和善。他看我很不自在的站在了他的渔棚前,能揣测到我这个小家伙肯定又是来偷他的瓜的。老人走出渔棚,笑眯眯地摸一摸我的小脑袋,就下了瓜地,摘了二个大水瓜给了我。后又让我上了渔棚前河面上的一只小木船,将我护送了回来。老人不停叮嘱我:下次不准再来了。我捧着大水瓜,连连点头。
某年秋天的晚上,我和伙伴们得知河的对岸五里开外的一个叫“刘营村”,放映战争片《地道战》的电影。我们几十个都在十几岁左右的偷偷结成伴,瞒着家人,在天黑后,跨上堤圩,越过树林,来到河边,跃入凉飕飕的河水里,趁着夜色的月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我们经过了一通的折腾,游到了对岸。提着衣和鞋,光着屁股,赤着脚丫,走在银色的月光下,走在高高低低、道道坎坎阡陌的田埂上。我们摸到那个村庄时,电影早放了。散场,折回,夜色渐浓凉飕飕,又游了过来。现在想想,恐怕再给我一百个胆量也不敢的。
我八九岁时,从不知人间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整天围着个村庄四处乱窜。村庄是我的天地,田野就是我的乐园。
在那食不果腹的年代,我们只能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天生一副的野性与胆量,整日忙碌奔波于广袤的田野上来获取我们所想能得到的营养。这里的水,滋养了我们的先辈,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也培养了我们孩提时的聪慧。学会游泳成了我们的天性。出门不远,便是大河,小河,水田,灌溉渠。有水,就会有鱼,有虾,有螺蛳,有河蚌和蚬子……样样皆是不错的乡野美味。大人们也从不需为我们担心过。这就是水,赋予了水乡孩子们应有的野性。
母亲为了从小就开始培养我超人的胆量,7岁时,就让我独自去村子的南边,跨过一条大河,一座摇晃不定的小木桥,送午饭给在田间劳作的我的大哥。我记得第一次上了那座小木桥,没走几步,木桥就吱吱嘎嘎,摇晃得厉害。到了中间,进退两难,竟不敢往桥下看一眼,吓出了我一身的冷汗。
后来,母亲知道我还有这份子的胆量,就让我去得多了。白天去,傍晚也去。白天走着过桥,傍晚爬着回来。印象中,那边有一块长满荒草的空地上,长着几棵高大的槐树,槐树的下面,埋着几座野坟。树顶上,一个挨着一个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鸟窝。白天走近,总觉得阴森森恐怖。夜晚经过,突然从树顶上飞出个喜鹊或乌鸦或猫头鹰,让人毛骨悚然。风大或下雨下雪时,看着这座桥,一筹莫展,只能望桥兴叹。
每年的暑假,想开个荤,我准会提着篓子,拿着提罾(一种里下河人取鱼的工具),走过那座摇晃不定的小木桥,踫在稻田里,水渠里,小河边,取鱼、摸虾、拔茅针、摘蚕豆,或被我母亲安排去割猪草。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培养出了我今生的胆量,以至于我现在哪怕是在细雨蒙蒙的夜色里,一人走在荒郊野外或坟茔堆里,我从不曾惧怕过。
村上人想走出这“荷叶地”,别无选择,只有跨过村西的那条河了。这30多米宽的河,把一个原本为一个自然村,隔成犹如东西的两半球。双方彼此接触往来甚少。那边两个生产队,90多户人家,以王、陈两姓居住着。我们这边四个生产队。这条河虽然不宽,但水倒是很深。由于在村的西边,人们就顺自然叫它为“西港河”。“西港河”上早年没桥。只一条小木船,风里雨里云里雾里,孤寂地漂浮在河心的当中。小木船的两头,各系着根草绳。草绳的两端,系在东西岸上的两棵树根上,供来回的人,蹲在小木船的一头,自己牵引着渡河。到了刺骨的冬日,草绳冻得硬邦邦的。有多次,我曾在寒冷的冬天的大早去上学,在渡过这条河时,被硬邦邦的草绳冻得手指头发麻难受。后来,村上的干部为了安全和方便,便在这河面上建起了木头桥。它由八根木头桩,几根长短不一的横木拼着,就成了一座村上人进出的必经之路的桥。这桥走上去,好像比村子南边的那座桥,摇晃得更厉害,吱吱嘎嘎的声更大更可怕。听大人说,是河水深,桥桩细而又高的缘故。每当遇到刮大风、下大雨、下大雪,总瞧见老人、妇女、小孩,尴尬地从桥面上,爬过去或爬过来。
一日夏天,听说那边有个姓王的老头,上吊死了。好奇的我们,看热闹回来后,突遇刮大风下大雨。我们都是从桥上爬了过来。有几个胆小的,竟然站在了对岸哭了。
童年时,最值得我回味的,当数村庄北面的那一片很大的开阔地。开阔地的中间,有一弯弯四米多宽的土路。土路两侧是又深又大的水渠。小时候,我们常在这水渠边,放风筝,摘野花,拔茅针,麦田里,躲蒙子,稻田里,逮蚂蚱和青蛙……夕阳里,看火烧云,看村庄里的炊烟,聆听村庄里的狗叫声。
春天,水渠两边长着野草,开着野花,蜜蜂蝴蝶空中飞舞。人徜徉于此,犹如走进花的海洋。空气里,氤氲着特有的泥土芳香。水渠边,歪歪扭扭稀稀疏疏的杨柳妸娜多姿地吐出了嫩芽,柳絮一直伸垂渠面。
我们牵着吃草的小牛犊,或骑上牛背,或田埂漫步,或听女人们唱着动听的秧歌,男人们打着号子。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后,鱼儿乱窜,蛙声四起。我们拿上小提罾,那些鲫鱼,鲢鱼,长鱼,秋鱼……总会顺着沟渠流淌的水逆流而上,蹿到渠里,稻田里,窜到我们的提罾里。聪明的我们一回一个准,沉甸甸拿回家,美美的享受。
这坑洼不平的土路,弯弯曲曲延伸五百多米长。一直至北边的那个一百多米宽的东西向的“海沟河”。
“海沟河”,它是我童年向往梦幻的一条河。这条河,交通特繁忙。这宽阔的河的对岸不远,就是“新垛乡”的政府所在地。遗憾得很,“隔河千里远”。最羡慕吸引于我眼球的,莫数那来无影、去无踪,像刀子似的劈开水面疾驶而过的乡领导坐的那个“小快艇”了。
夜晚,“海沟河”的两岸,萤火点点,蛙声一片,波光粼粼,热闹而让人陶醉。忙活了一天的农人们,来到渔火点缀着的水面,来到清凉的河水里,嬉戏、疯闹皆有,这时总会忘了一天的疲劳。
秋天,站在“海沟河”的岸边,环顾四周,金灿灿一大片,丰收的喜悦,从大人们的脸上和矫健有力的脚步声中就能显现了出来。女人们挥舞着轻巧的镰刀,男人们的肩上,担着沉甸甸的稻把,担着丰收的喜悦。
捕鱼人在“海沟河”面上,聚集着小木舟,手握竹篙,双脚直跺着小木船上的簧板,吆喝着鸬鹚。只见那扎着根脖颈套的鸬鹚,在水面上,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扑打翅膀,叼着大小的鱼。用细长的竹篙,将叼到鱼的鸬鹚勾引上船,夺下鱼,再将鸬鹚抛入水中。当遇有稍大的鱼时,几十只的鸬鹚围攻着捕捉。场面甚是迷人,我经常一看就是大半天。
“海沟河”,她承载着兴盛一时的扬州市与盐城市大丰县的“白驹镇”,旅客往返的水上交通枢纽的必经之路。我常独自好奇地驻足于南岸边,看着那冒着烟囱的轮船,听着那扬州口音,开着扬州客船,从扬州湾头往返的“扬白班”的轮船。当轮船快要到了我们这儿叫做“葛垛营”的码头时,总会拉响三声悠扬的长笛。当轮船靠近码头的那一刻,那些背着行囊的旅客们,总是很有秩序地上下着。随着一声短促的汽笛声,当轮船棚顶上的烟囱里冒出一股浓浓的黑烟时,轮船的后面,翻滚着浪花,船的后身,猛然向水下一埋没,轮船就徐徐地离开了码头,调转了船头,向大丰县的“白驹镇”驶去。
我的童年我的梦,就在一天一年的梦幻中度过了我天真而寂寞的时光。我常在心里暗发誓:我一定要坐上这条神奇的大船,走出村庄,走向外面精彩的世界。
不知不觉冬天来了。乡村的冬天来得早,及其的寒冷。路边光秃秃稀稀疏疏的杨柳落尽了残叶,显得孤零零的顶着寒风。水渠边的泥土路,显得很脆弱。遇到下雨天,走在这路上,泥团粘得鞋底鞋帮寸步难行,拖得人浑身冒出热汗来。遇上刺骨的大冷天,走在这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脚下“咯蹦”、“咯蹦”的硬。
忙活了一天的农活,母亲坐在煤油灯下,忙个不停地为我们准备寒衣了。我们也会陪着母亲,一边做着作业,一边听着母亲絮絮叨叨,总觉得童年是倍感的温馨。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到了我高中毕业的那年了。
79年的冬日,我真正登上了从大丰县的“白驹镇”“串场河”方向开来的那条神奇的大船的那一天,我是接到县人武部去报到的通知,去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当兵去了。
当父亲陪着我跨上了“扬白班”的大轮船,在一声短促悠扬的汽笛声中,轮船里载着一位有着远大梦想的我,缓缓地离开了码头,离开了生我养我的“荷叶地”,向兴化的轮船码头驶去。从那一天起,我就算是真正地走出了有着“荷叶地”美称的村庄,走进了外面精彩的世界,跨进了我梦寐以求的绿色军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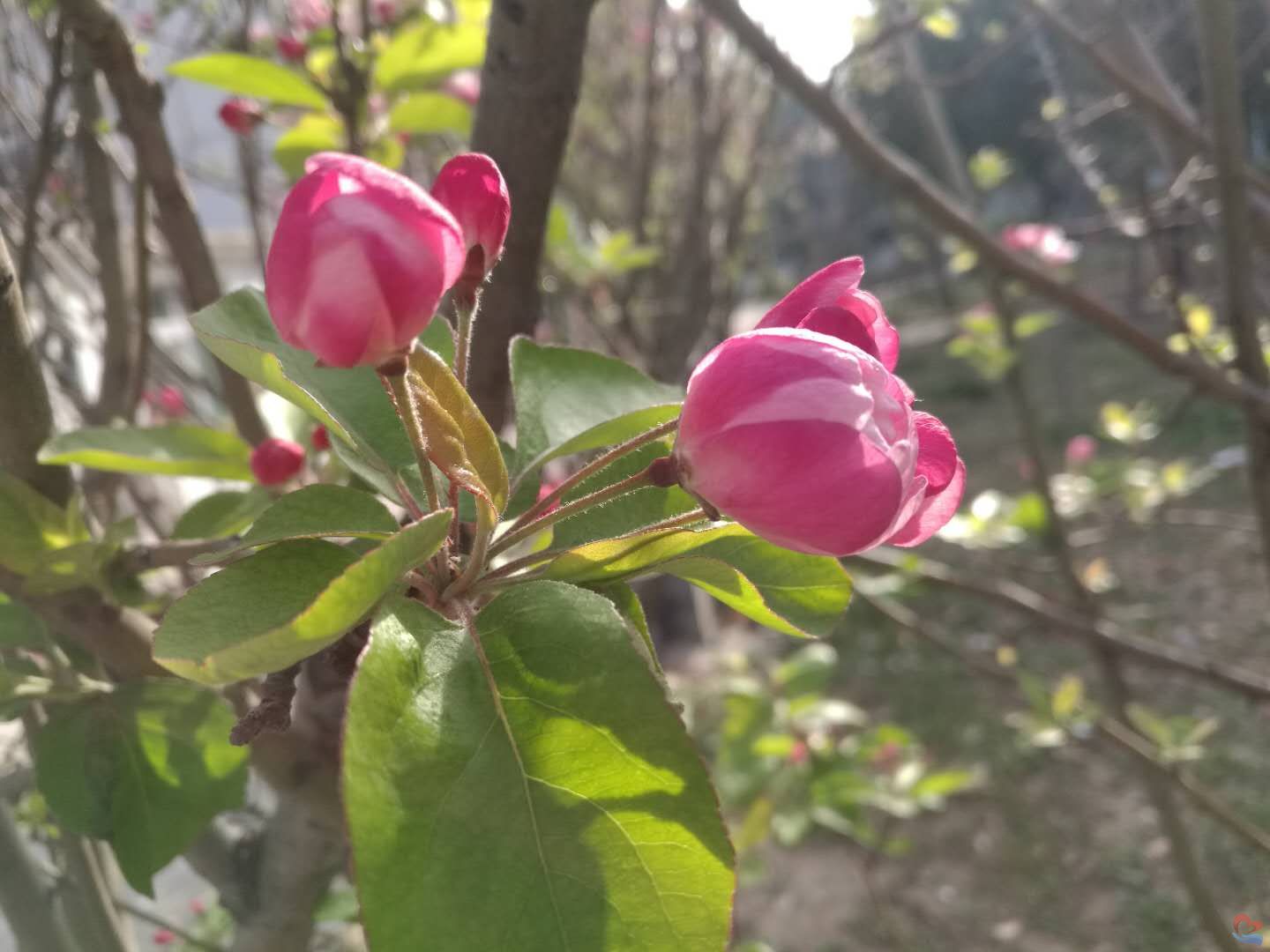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