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求神药
晚上,早点吃饭啊!妈妈说,爸爸没有吱声。我们几个小孩子也莫名其妙,不敢多问,就端着饭碗,手里的筷子不停地扒拉着。风卷残云,我抹了抹嘴巴,不情愿地离开桌子,肚子还憋着一块;到了这个季节,家里多是青黄不接,没有那么多的饭吃,总得闲着几根肠子。
我想到大队部院子里看看有没有小伙伴儿们来玩的。院子里,悄无声息的,我站着待了一会儿,正想走,喂!老张家的那个孙子,你怎么这么不孝顺啊!又是苟老四那张咧咧歪歪的臭嘴吧,我很厌烦。
怎么,还不理我?小逼崽子,等等。你奶奶有病,人家都在老赵家那个园子里占地方,等黑天了,狐仙下凡,好讨神药,你倒好,来溜达来了!这时,苟老四已经站在院子中央,与我仅隔着几米的距离。
讨什么药?我不解地问。
神药啊!听说,可好使了!苟老四神秘地说。
我不相信,那,你怎么不去呢?
我?我活蹦乱跳的,讨药给谁吃啊?
我想想也是,苟老四就那么一个轱辘棒子,无牵无挂的。
在谁家园子里?老赵家?
是的,快去吧!晚了,就占不着地方了。
我三步并成两步,大步流星地向老赵家园子走去。
小逼崽子,你急什么啊!不回家,拿个碗,搁什么装神药?
想想也是,就先回家,准备拿个碗。到了家,妈妈不在家,爸爸也不知道上哪里儿去了,剩下的哥哥、弟弟、妹妹,也不见踪影。于是,我想起妈妈让我们快点吃饭的缘故,敢情是占地方讨药。
等我到老赵家园子的时候,天放黑影了,只能看到脚跟前。园子里,静悄悄的,人虽很多,黑压压的,像苞米地里落满了黑乌鸦。我好容易找了一个地方,靠近园子门口,里面的好地方挤不下人了。靠着我两边的是陈老抠儿,还有史拽子的老婆。我厌恶史拽子的老婆,看到她,就想起她坐在地上干嚎,然后尿了裤子的情形。想到这些,我就慢慢地挪了挪地方,向陈老抠儿贴近。挤什么?小东西!陈老抠儿小声地说,我看见他的那个可以扣下来的眼珠子了。
不要说话,跪好了!不知谁在黑影里,严厉地说,声音不大,却很有分量。跪着吧!我来的时候,就看人家都跪着,自己也顺势跪着,膝盖下面有一个小石子,硬硬的,咯得生疼。我慢慢地挪了一下,这回好些儿,是垄台上,土很软。放好碗,就等着狐仙来,施舍给我神药。
偶尔,还有后来的人,挤进来,有电筒,也都不敢打,摸黑进来,随便找一个地方,跪下,等着。
怎么还不来呢?有人小声嘀咕着。等着吧,来了,也看不见,就看着碗里有没有神药就知道来不来了。
不要说话!狐仙会怪罪的,那样就白等了。
我是不敢说话。本来不敢来,是苟老四说我不孝顺,我就要做一个孝顺给苟老四看看。所以,我很虔诚,默默地祈祷着,狐仙给我神药,治好我奶奶的病。史拽子的老婆更是目不斜视,闭着眼睛,佝偻的腰尽量地挺直着,嘴里咕唧着什么,听不清,像是念咒似的。
扑哧!扑哧!扑哧!
连续几声动静,不大,也不小,我的一左一右听得很清晰,有的人憋不住,笑声从嘴牙子边不慎跑了出来;还有人根本就禁不住:谁啊!放屁,这么臭!并且一个劲的在磕着头说:狐仙啊,你可不能给放屁的那家伙神药啊!
真他妈的胡扯!怎么整,狐仙今晚是不带来的了!陈老抠儿气哼哼地说,也就站起来了,将碗凑近那只好眼睛旁,惊喜地叫到:我讨到神药了!我讨到了!他这么一咋呼,园子里就开始了乱哄哄的,如果说刚才是一湖平静的水,那么此时,已经是海浪汹涌了。
是吗?真的吗?我怎么没有呢?
……
我很好奇,看了一下我的碗,空空荡荡的,站起来,翘着小脚,看陈老抠儿的碗,星光下,他的碗里,有几条小细虫子还在蠕动着呢。
哪是什么神药啊?那是虫子!我说。
放屁!你个小逼崽子懂得什么!陈老抠儿急眼了,一只眼睛冒着恨恨的光,投向我。
我不放声了,端着碗,不知所措。
走吧!今晚是这么的了!
我也讨到了神药!还有人在其他的角落里,很是兴奋地说。
陈老抠儿屁颠颠地走了,捧着那只四边豁牙子的碗,像是捧着一尊神。
你的碗里,哪里就有了神药了,那是一层土!有人在质问刚才说自己讨到神药的人。
怎么是土呢?你睁开你的狗眼,好生看看,这是神药!别自己,心不诚,讨不到神药,就说我这是土!
我走近那个捧着碗的人,看到她的碗里,确实是有一层东西。而这东西,我的碗里也有啊!难道也是神药?我不敢肯定,却也不能慢待了碗里的那层土。
他妈的!谁拉的狗屎啊?又有人在骂着。不好骂人啊!有人在劝。不骂他,还能够便宜了他。怎么呢?不知道是哪个王八羔子拉的狗屎,让我摁了一手!真恶心死了!
狐仙啊!我不讨药了,就求你让那个随地拉屎的家伙,以后再也拉不出狗屎来,就好啊!
这时,一阵阵哄笑一浪高过一浪。
白来了!跪得拨了盖都生疼!
不要说丧气的话,让狐仙听到了,会不高兴的!一个说话嘴巴直透风的老婆婆说。
爱怎么的,就怎么的!我是不再来!我看就是纯扯淡!都愿意听陈老抠儿胡诌八扯的。说这话的是村里有名的老显儿,很爱显摆,也不听邪,绰号就叫做老显儿。老显儿平日里戴着军帽,帽子里塞着一块掸了廉价香水的手帕,头发抹了一层头油,有人说,老显儿就像小牛犊子刚刚从老母牛那什么里钻出来似的。
别人是这么说,而在外面小孩子看来,老显儿还是很潇洒的,是我们羡慕的对象,他一走过,香味很久才散去;即使香味并不怎么地道,咋闻还好,再闻,就头晕恶心了。
神药,没有讨到。可是,我毕竟为了奶奶的病,跪在老赵家园子里一个多小时了,算不算是奶奶的孝顺孙子,我不知道,反正,苟老四那里,我没有留下话把儿。
有些时候,我就天真而且很自私地想,苟老四什么时候死呢?这个老不死的家伙,硬实的很啊!
讨到药了吗?苟老四第二天看见我上学去,站在大队部的门口问我。
讨到了!谁讨不到,我还能讨不到啊!我不输给苟老四,有自然说有,没的也要说有。
扯淡吧!都是他妈的扯淡!什么狐仙不狐仙啊!苟老四望着我的背影说。我回头,看了看他,冲着他大大地吐了一口唾沫,那唾沫吐的很远,像一粒子弹,快到苟老四的脚跟前,才落下,发出一声细微的响声,我似乎都听得见。
站住!小逼崽子还敢吐我!苟老四蹲下身子,捡起一颗小石子,使劲地向我投来,没有打着我。
打不着,屁老遥;吃鸡蛋,长白毛!打不着……我用儿歌当武器,战胜苟老四。
过了两天,讨药的风过劲了;而我每次走到老赵家的那个园子,依旧是头皮一惊一乍的,看了几篇《聊斋志异》,那鬼啊,怪的,都拥挤着趴在我的枕头上,进入我的梦里。
几次三番,夜里惊醒,然后,就不敢再睡。爸爸说,到南炕来吧,靠着爸爸睡,就准保没事。
我迷瞪瞪地从北炕到了南炕,挨着爸爸。爸爸鼾声又响亮地奏起,我还是睡不着。妈妈说,儿子,妈妈下地给你那把菜刀垫在枕头下,就好了。
妈妈说着下地,真的拿来了一把明晃晃亮堂堂的锋刃的菜刀,塞在我的枕头下。不知为什么,我还真的就睡着了,那些鬼啊怪的,没有再耽误我睡觉。
菜刀的威慑力量真不小。我们小时候的儿歌就有:旋风旋风,你是鬼,两把菜刀砍你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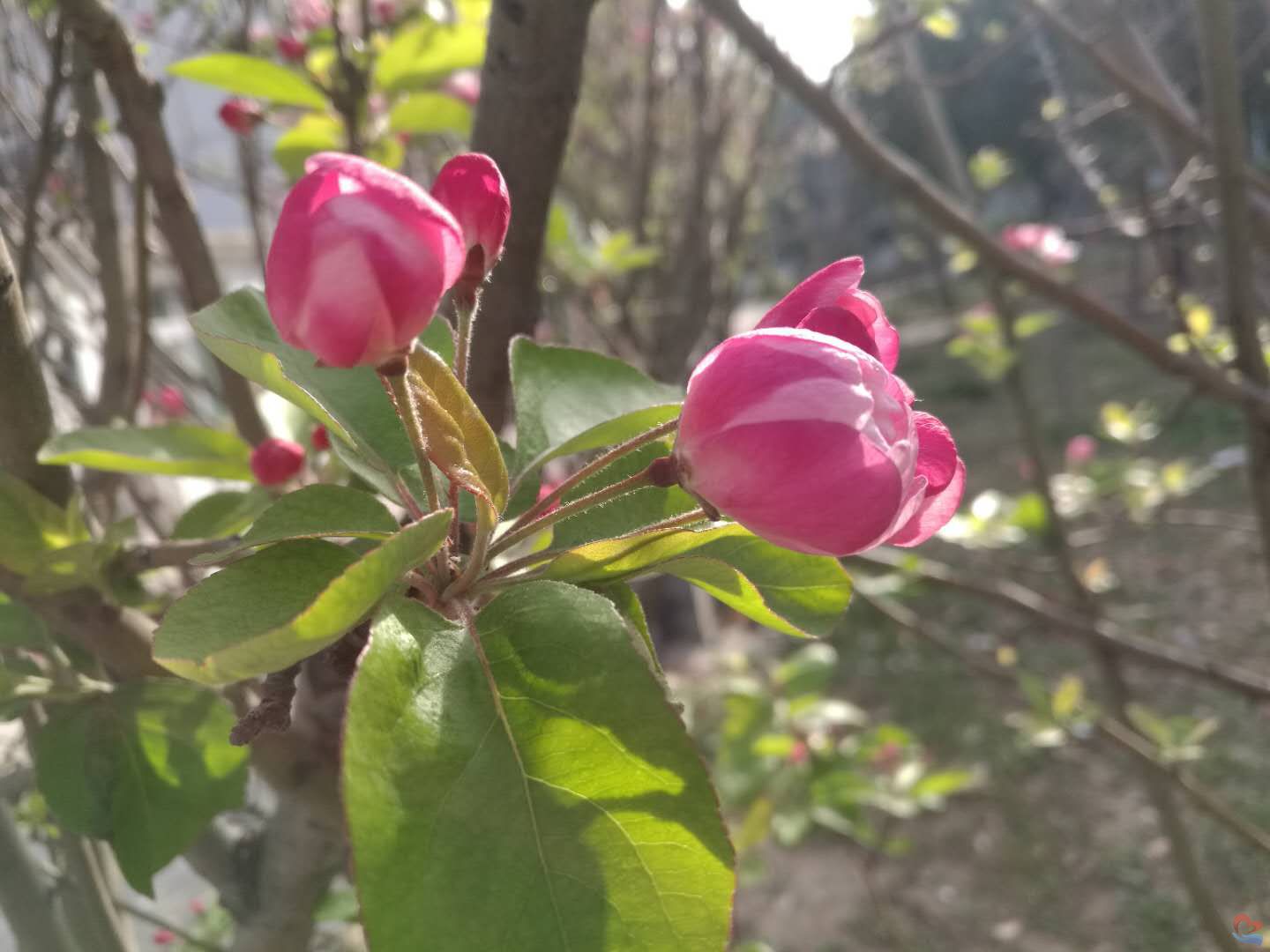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