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TOP | |||
|
荒城
管理
作者:甲申 发表时间:2015-01-26 09:10:25
评论:0条
关注
编者按:作者以深沉凝练的艺术笔触描写、揭示了改革开放初期南下打工族的生活画面及其精神层面。在历史变革的新时期,为了生计,打工、赚钱、养活自己已经成为一种锐不可当的趋势和潮流,打工族中的一部分人带有一种盲目性也是在所难免。到了南方开放的大都市,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加大,起初的迷茫彷徨,无所适从,进而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也开始了必然的变化。深圳筒子楼的各色人物刻画细腻,栩栩如生,人们的势利、虚伪、甚至冷酷、无情被作者描写的淋漓尽致。作者对于那个时期人们的内心世界剖析深刻:虽然身处繁华闹市,一切向钱看的目标明确,但是精神境界却酷似一片荒城。生活素材提炼精辟,故事内容凝练,令人深思。小说蕴含了无尽的思想意蕴。足见作者的文字功底厚重,艺术笔法娴熟。 |
|||
|
七月的日头当午,太阳的余热被一缕昏暗阻挡,地上面依然有埋葬在烘烤过后的热浪的痕迹,我还是没有见到有雨季来临的任何征兆。在筒子楼里面的每一处过道,都遗留下每一个倥偬而困境的脚步声,地面被洒上了水也阻挡不了热气。我与每一个住处的人擦肩而过,每天,我就与认识的,不认识的人这么打招呼。我的头上面止不住的汗水从各个方向流下,浸满了靠在墙边的四方木桌上,瞬时被烘干。过道上,除了女人以外,男人们都光子膀子在水泥地上穿梭。老张把旧框的老花镜别好鼻子正中,把报纸放到另一只手上,使劲地朝袒着乳的胸前摇曳着芭蕉扇,而眼前则录播着录音机里面的最新的上海独角戏;老张的愣儿小张我从小认识,这次南下广东我是打工,他是任职。他在屋内阳光的曝晒下露出臂膀,肋骨和筋条的形状像在一根树干一样,他瘦削的脸上驾着一副新款的小镜片眼镜,是八十年代新流行的产品。自八年前的全国统考以后,他更不和我交流了,小张毕业以后得到一份踏实的国企工作,这些天他应该都是忙忙碌碌的样子,不忙的时候,在家里我也是打扰不得他的。他正注目的看着书,只是用手不住的擦着臂上的水,把书本上的钢笔字迹弄脏了,这天气太热了。 我有一个和这个季节相符的名字,又觉得“夏天”这个名字太过朴素,以致被热浪烧心,烈火焚身的劳苦命终身。八十年代的夏天,我离开了苏北的山区,不再想被联产承包的计划生活所累,几年前刚恢复高考,以我恬不知耻的水平居然也蠢蠢欲动,亲身经历的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所以,我觉得车间里面的生活比较适合我,打工,赚钱,养活自己最重要。 其实,在这深圳的筒子楼里面,我也只是一个过客,作为一个从偏远城市奔来的没文化的打工仔,因为口音的冗杂,我自然只能混迹于三教九流的社会环境里面。外面的机器声还是一样,是挨得较劲的不远处工地传来的,日夜不停的运作,作为八十年代未来希望的沿海城市的开发圣地,天空的昏暗俯视着苍凉的一切。我知道我的脚下的土地只是一段短暂的休憩,我刚刚打开录音机,把手巾放在被汗湿的肩上,正准备听崔健的摇滚的时候,被房东太太一再催促着那气管炎的敲门声所打扰,工作了一天的晚上,到这个临时的家里还是无法消停,我已经不想再留恋这个聒噪的地方了。 “吵死人了,夏天。”有人对我吼道。不过之后就不这么说了。 “吵死人了,死尸!”我被隔壁的一声詈声震慑住,是另一种对我的口吻,这大概是小张邻居对我的日常用语,今天他不在单位宿舍,而是在筒子楼里面。 今天我买了几张半市斤的粮票和肉票,小心而谨慎的把这些“朋友”叠好再夹到上面印着列宁格勒图案的花黄的日记本上,这日记本上我很少动笔,只是用来涂鸦和记账用的。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晴。日用三块五。”“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日,星期五,日用七毛……”我翻来翻去,除了几个数据就是数据下普通的日子,要想改变这一切,只有不停地往车间的流水线上跑。夜晚,我突然听到风的声音,暂时让楼里与外面开始宁静而安详。窗户外捎进了雨水,气候是时候朝着沿海的水汽的心情而走。今晚,我居然盖了层被子,极热的天气下是极冷的凉气,我仿佛冷到了冰点。夜里我听到了雨水拍打在屋檐与水泥地上的声音,工地桩上的机器矗立在低矮的厂房和大字牌的标语旁,它们被世界的屋角盖住,像疲惫的旅人沉沉的安睡。 我醒来后大概已经是三天后,衣服上已经没有汗渍,身上无法感知燥热,荒凉与寒冷却被侵袭。日历上还是七月,我吃力的看了看,我已经误了三天的工厂的流水作业。 反正一开始我就听着小张的骂声了,这个从小认识的小张现在是我单位的科长,自然官大气粗,我也没办法。没事的时候,与我也无话可说。 其实早上我是被筒子楼里面的吵闹声围住,我想深圳的这些旧址即将被拆迁的时候也不会忙碌。不是因为别的,是住在我隔壁的I君,死在了自己的简陋的卧室里面。说是卧室,其实就是和我一样的三十平米的小房间里面,我不知道在雨夜的雷鸣里面听到些什么,也不知道在极度燥热的空气中他吐露过什么,只看见他的脸上是一副扭曲到极限的形状,事后有说闷死的,也有说心脏病死的。可我分明看见他的脸上的梦魇,不规则的黑褐色布满阴郁而冰冷的脸上。我想要不是房东太太,谁也不会知道他在五天前就已经去世,尽管他的房门紧闭,屋内被七月的空气挤压发出恶臭,旁人只会无奈的走过经营自己的事业,把窗户用力的栓好。谁也不会去怜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即便认识,那又怎么样呢?I君的死亡证明开出以后,我有一种不自然,我没看到他的亲人,谁也没有留意他的死。他们只说,这里有死尸。骂活人时如此,死了倒真成死尸了。 当然,我也一样。谁也没有留意我这样活着,卑微还是高大,都与人无关。早晨我只是按照惯例洗完头,凉水的冲击让我精神抖擞,几分钟以后,蓝色的工厂厂服又被热汗渗透,雨水以后比之更加闷热的天气依旧,让人无法呼气。 来到工厂,我被小张劈头盖脸的批评,写了检查,就差写辞职报告了。回到家的筒子楼旁,我看到老张,我打算和他打一下招呼,我觉得他年纪大了耳背,所以我对他说了三分钟的话,他一句都没有理我。至于小张,连正眼都没看我,头也没抬起来,只顾着在看书。 然而出门在外,总会认识几个人,就像几年前刚来深圳打工一样。而I君则是我在筒子楼里面认识的其中之一,也许仅仅是因为邻居的关系而认识,但我想我们应该是朋友。 以前的夜晚,我总是游离在工厂车间与筒子楼里面,戴着袖套和蓝色的工帽,像机器一样回家,吃饭,睡觉。我洗了三十分钟的手,浪费了八千毫升的水,终于把手上的机器油污给冲洗干净,疲软的躺在一米宽窄的依靠在墙上的木质床上,等待明日的闹钟把我唤醒。 其实几分钟就有声音把我吵醒,这是隔壁的屋主人的惯例。不是锅碗瓢盆,倒是一声声的乐器传来的声音,无奈的只好让我捂住耳朵使劲敲墙。 “咚!”我终于使劲的揣了几下他家的木门,声音总算消停。可是等我转身回到租住的房子里面的时候,声音再次响起,自然又是临门一脚。 我暗自得意,没有了声音,门却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稚嫩的面孔,头发粗糙没有打理,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T恤,鼻梁上戴着一副宽边的眼镜。这是一副穷酸的知识分子的样貌,他年龄估计和我相仿,在二十多岁左右。他或者在哪个科室上班,又或者在哪个学院上学。当然我没好气的冲他嚷嚷,他只是愣愣的,一直没有回答我什么。我看到他屋子里面摆放着一把手风琴,这应该是刚才吵到我的声音所在。 “大晚上的,以后别吵。”我瞪了他一样,夜色已经变暗,楼道灯光也很暗。他对着我傻傻的没有说话。 “死尸。”我转身骂完以后,喝了一口搪瓷杯里面的开水,终于睡去。 他就是I君,至于我叫他I君的来历,那已经是后话。原因是他档案的identity的首字母而得,因为他的名字写得太过潦草,以至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所以我只好这样写。当然得知他档案的信息,只是因为他也是我的同事的原因,这完全是之后才知道的事情。 好多天,我都会在下班的楼道里面看到他,我不以为意,他也如此。我想作为陌生人都是这样,只是认识他以后,他还是一头愣愣的雾水,根本不说话。又一次,我在筒子楼里面的小饭店里面看到他,他独自坐在一个人的角落吃着米饭。我手里拽了一张一两粮票和五分钱,打了一份油条的便当,坐在他的面前。 “我说,你这个东西沉不沉。”我看见他的肩上背着一把略旧的小吉他,背带上勒出一滩汗水,“你喜欢听音乐?” I君没有说话。 “说实话,那天我敲你门骂人是我不对……”我想了想,觉得应该向人家道歉。 他只顾着吃着饭,头也不抬。我就这样无趣的自问而没有自答。因为每晚能从隔壁传来吵闹的音键声的缘故,反而引起了我对他的好奇。 “我说,同志……”我张出一只手,继续打算和他友好地搭话。可他却站了起来,完全没理我,吃完饭撂下筷子走开了。 我突然怀疑他性格有问题,甚至怀疑他是个哑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直觉是对的。 其实对于他生前的很多事情,我还是不得而知,我们都在扮演别人眼中的匆匆过客,谁都无法走进谁的内心世界。 那天I君被火化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的母亲,鬓发已经非常的白,I君的母亲一动不动,眼睛里已经没有泪水。她跟我说她其实早就知道I君的心脏状况,但其实很长时间,我都不认为I君有心脏病。 但没法改变的是,我的夏天很冷,对于我的名字也一样。 我几乎好几次撞见I君,I君的眼神,我看得出来是没有精神的,尤其是一直闭口缄默的样子让我无法不好奇。有时候,我会拍一下他的肩,他却像一张白纸一样,苍白而无力。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只是与他擦肩而过。最后,我还是想到自己的生活,我还有一个月的房租需要解决。那天,我碰到了一口粤语的体型臃肿的房东太太。 “我想和你打听点事?”我把几张纸币递到房东太太的手心,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她的手掌,我说,“就在我墙边挨着的,就是我的邻居,你知道他是谁吗?” “谁?”她的眼睛没有看我,像是心不在焉的敷衍了我一句。 “就是一个戴着大镜框眼镜的年轻人,喜欢在夜里拉手风琴,他经常吵到我。他大概和我差不多,二十多岁的样子。”我说,我站在她的门外,穿着背心被热烈的七月日照的汗水腐蚀。 “哦。那怎么了?” “我想,当有人吵到让你无法休息的时候,你会和他争执吗?”我一本正经的说。 “各管各的,谁顾得上谁啊。”她没好气的和我说,马上就要关门。 “唉,等等。”我制止了她,房东太太给了我一个怒不可遏的眼神,“我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他这里有问题。”房东太太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他是一个神经病。” “神经病?”我大惑不解,日光照在我的脸上,肌肤被曝晒成一团黑褐色。 “是啊,他脑子有问题,所以和你一样。”在我不解凝想的时候,房东太太把门关上,发出很响的声音。 我愣愣的站在远处,想了想,大概是如此。说实话,我每天傍晚回家,推着自己那辆二八凤凰自行车遇见他,仅仅也因为脸熟,除此之外,根本不想说别的。所以等到夜晚被音乐声音吵到不行的时候,我才会去敲他的门,别无办法,除非他在弹最新的崔健的音乐我还听上一会。 我不知道夜里他在拉弹什么,却总是不唱。直到有一天,我在工厂看到他,才知道他也是我的同事,而不是某个学院的学生。他的工作服很脏,看得出来他在操作机械方面不是很熟练,我走了过去拍了拍他蓝色的工服。 “我来帮你吧。”我扯开了嗓子对他吼,车间的机器声很吵,足以让对面一米的人听不见声音。他愣愣的看着我,配合这副眼镜像个傻子,我接过他手中的板子,替他拧好了螺丝,他就一动不动的看着我的背影,不说一句话,当然他的话也许我没有看见。 我想他是刚接触工作的年轻人,只是很少与人交流罢了。在工作之余,老同志和年轻人的群体里面好像很少有人和他在交流。那天我看到I君在宿舍进进出出,我准备进去,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里面很安静,就摆着一副吉他。我看了看桌子上摆着一些数字一样的排序,和跳动的符号一起串联成一段段声音。其实那就是曲谱,只是我根本看不懂,上面的五线谱像一条条充满希望的悠扬曲线,的确可以在工作之余放松身心。 “你,出去吧。”他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的身后,我转过身看着I君的戴着大边框眼镜的痴傻的样子,他穿着一件汗衫站着。 “这宿舍怎么就你一个人。”我不解的问他,“原来你不是哑巴,我一直以为你不会说话。” “我叫你出去,没听见吗。”不容我说话,I君继续不知好歹的厉声说。 我不知道原来他是这样的人,除了让人心生不快就是让你憎恨,我想怪不得他会没有人缘。从任何角度分析,他就是一个哑巴加傻子无异,纯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神经病。”我撂下这句话就走了,我想我没必要和这种人套近乎。 在筒子楼里面的过道上,我时常会看见他,他的出现会让我吹着的哨子停顿一会,然而,我与他擦肩而过,我的眼前的目光根本就把他这个人剔除掉了。 过了几天,天气晴,六月底。这些天,我一直没看到I君。 “小夏,你知道吗。今天你在我们厂里面被评为先进标兵了。”孙师傅探出头,对我笑着说,孙师傅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是工厂的门卫,也是我的苏北老乡,因此乡音总能让我在异乡感到亲切。老孙他眼睛不花,头发上还是浓密的黑色,很有精神。每次看到他,自己也矍铄起来。 “你好,老孙。”我笑着跟他打招呼,从工厂出来,反正都把喜悦挂在脸上了。这是我南下深圳的第一笔财富,我自然想把七月的燥热散去,属于了一个和自己名字一样的真正的夏天。我穿着蓝色的工帽和车间服,戴着袖套的手推着二八自行车,把它停在老孙的面前。 孙师傅开着录音机,他也玩起了这些新鲜玩意儿,里面的最新的香港明星歌曲他一曲都没有收录,全是和村里面大喇叭广播差不离的声音。“呦,老孙。你也赶了新潮,可计划赶不上市场。哈哈,你的思维还需要新一轮的开始,不是改变形象就能改变的了的。”我没事总喜欢和孙师傅开玩笑,他打完开水,我坐在门卫室里,把一杯热茶递到我的面前。我总觉得七月的夏天开始变凉了,内心却温暖了许多。 “给,老孙。”我递给他一支烟,他习惯的别在耳肩上,呵呵的笑着,把下巴的胡茬卷起了一道笑窝。 “对了,小夏。你来深圳几年了。”孙师傅用苏北方言和我说话,我低着头笑着。 “也有好些年了,不过我忘记了是哪一年来的深圳。”我无奈地挤了挤嘴,嘴上叼了一根烟,升起一团雾,大概象征着什么,我一时又没有想出是什么。 “小夏,你未来有什么打算吗。”孙师傅舍不得抽烟,只顾着喝茶。 “我,我还能什么打算,攥着粮票过日子吧。” “你小子,呵呵。”孙师傅被我这么一说,笑了。 我也附和着笑,笑声飘散了夏天的暑气。 “对了,老孙。你知道我们厂里面的一个年轻人吗。”我对着老孙说。 “谁?”老孙颇有精神的好奇地说。 “就是每天在我对面的职工宿舍的一个小伙子,戴着宽边的眼镜。”我向老孙打听了一下I君的下落,算起来他有几天没有上班了。 “戴眼镜的……没什么印象。这厂里的老干部和一些年轻的同志大都戴着眼镜,我也不知道。”孙师傅抱歉的说。 “那么老孙,你有没有看见过我们车间的一个小伙,平时喜欢背着一把吉他的……”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孙师傅稍有一点顿悟,“不过说实在的,这个小伙不怎么爱说话,是个有点上进心的同志,只是他们说他有点不正常。” “是有这么一回事,我有些天没看见他了,也不来上班。”我顿了顿,喝了一口茶,“老孙,你说他有神经病吗。” “我不知道,好像别人有这么说。” 可是我有点确定了,I君是个不正常的人。我想自己不能住在他的屋旁,他的存在,甚至让我害怕起来。 我推着自行车,笑着致意孙师傅,我准备下班回家,心情却不像原来那么无虑了。路上我看见那个我从小认识的筒子楼隔壁的小张科长,我笑着和他打了招呼。 小张没有回应我,继续和他身旁的同事说话,看来我的对话是多余的。尽管这个小张在刚才的表彰会议上对着员工笑着说我“夏天”的名字,但下班以后,他依然一句话都没有和我说。 回到家,我洗着袖套上的油污。听着水龙头的声音,夹杂着清悦的动人,让我听到“泉水叮咚……”的老歌的旋律,只是几分钟后却让我不寒而栗。因为是从隔壁的I君的房间里传出来的,我已经听不出来他在拉手风琴还是弹吉他。 这次,我居然不敢去敲他的门,我的心已经疑虑不已。更要命的是,我的房门却响了。眼前的面孔正是I君,他不像以前那样,虽然板起脸,却已经可以开口主动和人说话,他面对我的任何一句话都会让我震惊不已。 “你好,我姓徐,你叫我小徐好了。”我确信这是I君的脸,他和以前穿的一样,是一件纯白色的T恤,没什么不同,还是戴着大镜框的眼镜。他好像友好的伸出手,只是脸部表情却是看不出来。 “你……你好。我姓夏,我叫夏天。”我迟疑的伸出手,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姓,看来他想和我交朋友,可我并不这么想,我只想躲着他,越远越好。 “夏天,多么美的名字。是故乡的季节带来的温度吗?”I君感慨的说,他走了进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赶他走,像他那样,那可不行。 “说实话,我完全听不懂你想表达什么。不过小徐同志,我觉得……” “老夏,我这次想找你帮忙。”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打断了我的话,“我想让你为我的音乐填词,可以吗?”他拿出一盒胶卷,据说是最近他在深圳的一家录音店录制的,废了他好长的心血。我听了一段,有特殊年代的旋律,又有临海的香港乐坛的味道,深圳不光是一个地理的纽带,也是一个文化的交融圈,我这么想道。正如我听崔健的歌,短暂的摇滚可以让我释放痛苦与不安,什么都可以忘记。 “可我不会写啊。”说实话,这是我这辈子没有人给我的殊荣,对我这个大老粗而言简直无法想象,我不得不推迟。 “不。”他拿起一盒摆放在我桌边录音机的磁带,“你不是在听摇滚吗,我觉得你可以帮我这个忙的。”他突然微笑着,我看着居然起了个寒颤。 夜晚,我看着一团雾水的五线谱曲和那段音磁,完全没有了睡意。要是说我不能完成,担心他的精神问题,也许我就命丧这里了。我不止听到筒子楼里面的房东太太说过,那根本不是玩笑,有更多人说过他脑子有病,不然怎么会一个朋友都没有呢?我变得焦躁不安,全然没跟他说他没来工厂的事情,直到从隔墙听到他的手风琴的声音,像是南斯拉夫影片《桥》的音段,我终于沉沉的睡去,我的房门和窗都被我锁得里外三层。 第二天早晨,我无力的和孙师傅打了招呼,吃力地推着自行车,眼圈一直发红,身子像驻足在海水里面,一直站不稳。 “怎么了,小夏。看你心不在焉的,是‘先进标兵’的后遗症吗?”面对孙师傅的调侃,我只是无奈的笑了笑,至于这个苦闷的夏天,“先进标兵”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称谓,这之后的每一天都让我惴惴不安的。 “是这样的,是我们单位的小徐……”我对孙师傅说起了I君的事情。 “那个人,他已经被单位开除了。唉,其实我们都知道他脑子有问题,可自己不求上进,我们也没办法。”孙师傅无奈地捧着茶杯,摇了摇头。我手扶着二八自行车的把手,愣愣的站在门口。 那天我偶然经过I君的宿舍,破碎的吉他卧倒在柜子旁,看样子刚被砸过,里面的木屑零落在地上和鞋子上,我看到I君时已经在筒子楼里面听音乐的时候。说也奇怪,那天他邀请我进去听音乐,我的心态居然很好,或许是我已经把他当做了我的朋友的缘故。 我一直觉得I君很正常,可别人不这么认为,也许像房东太太说的,I君和我一样,都有问题。 我记得当时他说了很多话,I君的老家在湘西,可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好,我也没有留意他的点点滴滴。他只跟我说他热爱音乐,热爱的细胞植根在每一根琴弦上。话说回来,这些对我来说像天方夜谭,我只想着我的粮票,肉票和布票等等。 “对了,夏天。你对音乐的认知是什么。”I君手里抱着手风琴,很自然地坐着。 “我不知道。”我无奈的笑了笑。 “是一种信念。”他自言自语,也没听我说我什么,这几天我完全放心他的对话,我只是觉得他是一个活在自己内心世界里面的偏执的人而已,我不觉得他有精神问题。 “小徐,我在以前大食堂,大概在七六年左右。当时喜欢听《莫斯科郊外》《小路》这些,配合你的乐曲,我觉得又在回忆从前了。” “是的,音律会让你回到过去,回归温暖。”I君的嘴角露出微笑的神情,“正如这指间的灵魂,是世界上最华美的乐章。”I君用手风琴弹起了苏联歌曲《故乡》,用唯美的音符走进久别的战士的田园,里面的战友在拥抱着每一个故乡的亲人。I君说,他在倾听吊脚楼里面的送别,有故土的水,故乡的泪。 我想我应该也会把自己陶醉,但最终我只是一个消遣流行歌曲的世俗之人。深圳离香港很近,最近总能在市场看到最新的唱片,我问I君,他好像对此并不感冒。 “夏天。你觉得你梦中的夏天是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I君会这么问我,对于任何情境下盲从的认知的世界,我都无法解答。 “夏天,就是一股凉快的风。”我感觉和I君在一起交流,也会变得文艺。 “那么,我会为你弹奏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你来填词。”我感觉我这次想要为这首歌曲填词,我不知道这份勇气和冲动来自哪里,大概是一种对音韵的眷恋和自然的回归。当然,这些都是假的,只是因为音乐好听罢了。 “八月的季节/记忆深处/有昨日的风帆/追梦人的眼泪/化成一缕风/八月的季节/故乡里面/是土地的温度/游行者的脚下/踏下一行诗/夏天/走过/我倾听最美的乐章/夏天/梦过/我走进浅美的家乡/梦的清唱。” 我把属于《夏天》的歌词写好,仿佛花费了我毕生的心血。可是至今I君都无法看见八月,我不知道八月的夏天值不值得我眷恋,只想起我的生活只是夏天的一个名词,这个夏天从音乐中走出,它都闷热无比。语言再美,也抵不过时光,我还需要为自己生存。 I君的死,其实对于我而言,只是我茫茫生命途中一个逝去的过客。一个孤独的行人,和我擦肩而过罢了。那段时间,我始终只会看见I君独自行走,独自吃饭,我不会为他的孤独的生活而同情半分,我自己都无法怜悯自己。我时常这样想,我何尝不是一无所有。各管各的,谁顾得上谁。 I君把手中的风琴从肩上拿了下来,无奈的说:“录音机坏了,没录上。”我无奈地耸耸肩,表示我自己的录音机也无能为力,因为这几天我已经没有再听崔健的歌。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帮到I君,就从他已经把我当做朋友的面子上。只是他并没有提及这件事情,我也没问。那天,我硬着头皮走到对面隔壁的小张的家里。小张现在感觉不仅仅是我的科长那么简单,我再三的跟他说话,他都笑着没跟我说。今天他家里来了客人,穿着老号的中山装,开着猛烈的电扇。他一直对着客人笑着寒暄,我又一次充当了空气。可明知我不该来,我还是来了。 “姓张的!”我终于用苏北话大声的对着他吼道,“你借不借我录音机!”这次我打破了他们融洽的气氛。 “不借!出去。”他眼镜下面的目光非常冷峻,我自然转身走掉了,这是他对我的有声回应,要是有录音我会把它好好珍藏,这是一份珍贵的回忆。 “这是谁啊,素质这么差。”我的背后是他客人的声音。 “是我的员工,就是经常和一个神经病在一起的那个。”我听到小张的声音。 大概这天以后,我也成了“神经病”的代名词了,所以很多人对我敬而远之,孙师傅是个例外,只要见到我,他还是一口苏北的乡音,对着我笑。 “小夏,出去啊。”孙师傅捧着搪瓷茶杯,很和气地对着我说。 “是啊,老孙。”我笑着推着自行车,和他对话。我骑着自行车,向前归去,我想自己应该好好地睡一觉,把所有的不安都忘掉。 筒子楼里面依然很吵闹,周边被工地开发的声音时常传来,我的睡眠再一次被无情的冲击。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变得郁郁寡欢。 我不知道I君离开了单位,去了哪里上班。在他去世的一段时间,他的房间被清理的干净,纤尘不染,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筒子楼的角落都没有人敢来租住,尽管房东太太已经把租金降得很低。 我没为I君借来录音机,但他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不过,对于小张,我已经把他从我的记忆里面彻底删掉了,在单位,看到他我也选择无视。 I君的行踪总是神出鬼没,说他是怪人也不为过。我很少看到他有正常的交流与社交活动,直到某天我在楼道的过道里面撞见了他,非常突兀。只见他梳理了头发,变得很整齐,三七分明,眼镜框也焕然一新。 “小徐,你这是处对象去了吧。”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大笑着说。 他一脸漠然,怔怔地看到,目光中带着疑惑与不解。最后他像一个陌生人一样,眼神非常空洞,我只好走开。 我感觉我受到了欺骗,原来沟通与交流是一道假的桥梁。无事不登三宝殿,只有有事的时候,会有人找你,不然就是一个陌生人。 我烦闷的打开收音机,听着当天的新闻,像一头无头苍蝇一样光着膀子呆坐着,一直坐了好久。 我和I君的误会几天后就解除了,如果在刚刚遇见他的时候,我想我断然不会与他再往来了。其实那天I君是去听音乐剧,怕别人误会我,就没有理会我。我想也是,在深圳的街区,已经有繁华的景象,对于音乐剧,对于我这个粗人,还是个新鲜的词汇。就像I君的identity里面包含了未知与未解。 I君把一把陈旧的吉他放在我房间里,他离开后的几天,放着一盘录音带。我听了听是当时他弹奏的曲子,他已经录成了,我觉得这算是他小有成就的第一步,比我这个庸碌的人强多了。 这就是那首《夏天》,不知为何我清唱了起来,像是世界上最美的乐章。我仿佛忘记自己的名字和这烦闷的夏天,只有音乐才是真正的季节的表达。 I君丢下他的吉他,又好像人间蒸发了。那段时间,我在厂里被人议论,居然让我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我觉得我被自己封闭,变得无法正常的交流,无法沟通,就像I君一样。不吐一个字,用拒绝代替了对话。 有时我突发地想到,小张是不是当了科长的毛病也是这样,我不得而知,我无法说他是神经病。这个世界,像I君这样的神经病活得自然,我就像一个死亡的灵魂在哭诉与飘荡。 大概是七月初,我才从夜里的隔壁听到他的声音。原来他这几天去了一趟老家,回了湘西。可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了无数次的狰狞,被生死边缘挣扎一样。他不再很自然地弹奏乐章,只有脸部在抽搐。 灰白的地上散落着一地的白色药片,他说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他就被心脏病夺走了黑夜的梦里。我不知道他的病史,也不知道他的痛苦,只是他无数次的对我说过音乐能让他忘记痛苦。 其实算起来,我和I君还是同届的考生,我们都在一九七七年参加的统考。他作为艺术生的骄傲被现实而妥协,但我却是一幅玩世不恭的姿态。可是工作以后,我变得安安分分,他却玩世不恭。我想,音乐会变吗,还是人在变? 在I君走后的一段日子,我几乎也拾摭起他放在我房间里面的吉他。我把吉他交给他的母亲,她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在不停的抽泣。我说,这是他生前最珍贵的朋友。 无论我再怎么弹奏,也弹不出最美的乐章。我被夏天的诅咒所累,被夏天的攻讦所屈,夜里我用一股冷水浇在我的身上,企图洗走我身上所有的痛苦与不安。我知道,这个夏天依然燥热与苦闷,外面的桩机愈发地响,开始刺破我的耳膜,我的记忆一片眩晕。醒来,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冷漠。 “小夏,你真的要离开单位吗?”我推着自行车,穿着一件干净的T恤,在传达室的门口孙师傅对我说,“无论别人怎么说,我觉得你都很用心。” 我笑着,看着老孙。我想他永远都是一样,对出行工厂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微笑以对,可别人永远不会用微笑对你。也许,我永远做不到老孙那样。 老孙说张科长没有批准我的辞职报告,希望我留下来。我知道老孙一直在安慰我,事实就是这样。 我来到筒子楼,准备搬走属于我自己的行李。不知为何,筒子楼变得很热闹,和原先不太一样。配合着当地的快书和歌仔戏的音乐,是一段很轻松的搞笑曲子。小张穿着中山装在和搬运工人一起把家具往下抬去,而他们都只穿着汗衫,被八月的热流渲染,汗水从衣服里面湿到胸口外面。下楼时,我与一身轻装的小张擦肩而过,我就与认识的他和不认识他的擦肩而过,没有说一句话,他头也没有抬。其实那天,他一早就把我的辞职报告批了。张科长从筒子楼里面搬走了,他已经是张主任了。 八月的季节,没有风。 “八月的季节/记忆深处/有昨日的风帆/追梦人的眼泪/化成一缕风/八月的季节/故乡里面/是土地的温度/游行者的脚下/踏下一行诗/夏天/走过/我倾听最美的乐章/夏天/梦过/我走进浅美的家乡/梦的清唱。”我清唱着,把上次小张落下的这张录音带放在他的坟茔前,我拿出一张从我衣带里面叠好的信纸,里面写着我的词。记得他说过让我填词,我写给了他,续上了曲谱,放在他的面前。不知为何,我现在会熟络这么一段五线谱,不知道五线谱的世界里面是不是一座荒城。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想到自己的思路,远方该怎样去走。我想着自己从一无所有的来,到一无所有的离去,生活让我变得简单。我始终想,I君并不是死于心脏病突发,而是间接的死于抑郁症,就像我一样,长时间的选择用封闭自己来拒绝别人。现在,我已经不再与人正常交流,感觉八月的夏天变得冷清。 窗外,下着雨,把夏天的季节冷却。我却想把夏季变热,可是内心始终出不了汗。 我拖着行李箱,在一家食堂吃过午饭。在深圳的很多地方,已经不需要再用到粮票,八十年代的生活在形形色色的波浪卷的发型和披头士的披肩发的世界里面流行开去,我与他们都是陌路人,无论如何,我都得离开筒子楼。 筒子楼旁被繁重而喧杂的机器声覆盖,它就像一个濒临老去的历史被埋葬。筒子楼里面的住户已经悉数搬走,这里正面临着拆迁和改建。 我离开一个地方,从另一个地方开始,追寻另一座城市,面对一无所有的音符,依然是一处荒城。 我走的时候,见到了房东太太,他一脸臃肿的体态,一口浓重的粤语还是让我记忆犹新。算起来,我还忘记了一件事,我忘记把八月的房租交给她了。只是她没提起,我也没记起。如果按她的话说,各管各的,谁管得了谁啊…… |

|
|||
| 【投稿】【 收藏】 【关闭】 | |||
|
|
|||
| 上一篇:龚生卖字画 (民间传奇) | 下一篇:夕阳下的牧羊笛 | ||
| 推荐美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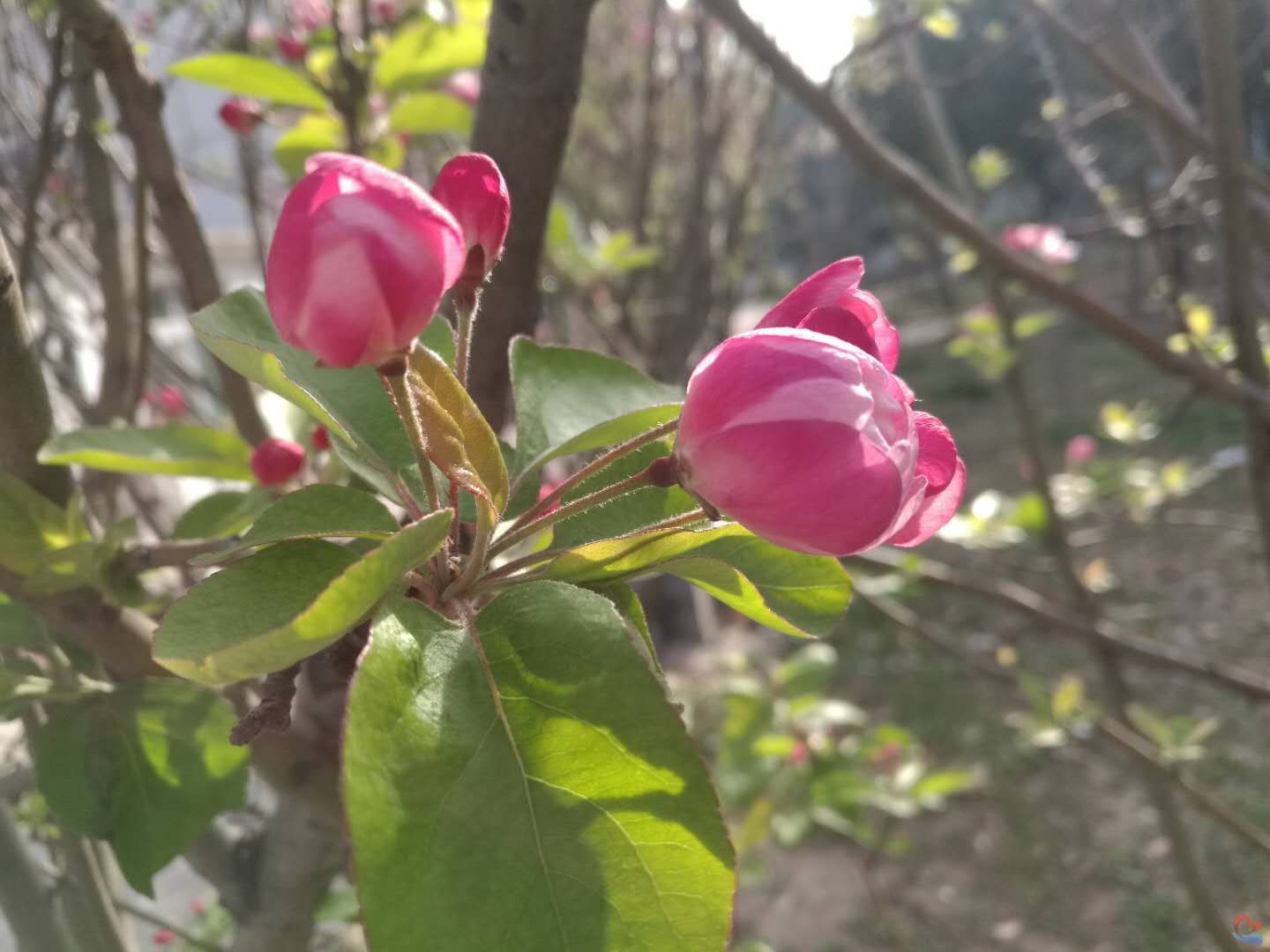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安徽 · 网络文学第一网站Inc All rights reserved.